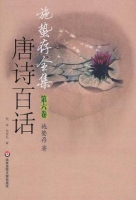东皋薄暮望,徙倚欲何依。
树树皆秋色,山山惟落晖。
牧人驱犊返,猎马带禽归。
相顾无相识,长歌怀采薇。
王绩,字无功,绛州龙门(今山西龙门)人。隋大业末,官为秘书正字。因不愿在京朝任职,就出去做六合县丞。天天饮酒,不理政事。不久,义兵四起,天下大乱,隋朝政权,有即将崩溃之势。他就托病辞官,回到家乡。李唐政权建立后,武德年间,征集隋朝职官,以备选任。王绩还应征到长安,任门下省待诏。贞观初年,因病告退,仍回故乡,隐居于北山东皋,自号东皋子。王绩与其兄王通,都不热中于仕宦。王通隐居讲学,为河汾之间儒学宗师,著有《文中子》。王绩以诗赋著名,其文集名《东皋子集》。
隋文帝杨坚结束了南北朝对峙的历史,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上统一了中国。南北两个文化系统,逐渐趋于融合。但是杨坚的政权,被他的荒淫无度的儿子杨广断送了。统一的新文化.没有来得及发展。在初唐的几十年间,唐代文化,特别是文学,基本上是隋代的继续。
王绩生于隋末唐初,文学史家一般把他列为最早的唐代诗人。我们现在选讲唐诗,也就从王绩开始。《野望》是王绩的著名诗作。这首诗一共八句,每句五字。古人称一个字为一“言”,故每句五字的诗,称为五言诗。第三句和第四句词性一致,句法结构相同。第五句和第六句也是词性一致,也是句法结构相同。这样形式的结构,称为“对字”,或称“对偶”、“对仗”。每二句称为一联。词性一致的对句,如“树树皆秋色,山山惟落晖”,称为“对联”。上、下二句不对的,如“东皋薄暮望,徙倚欲何依”,和“相顾无相识,长歌怀采薇”,都称为“散联”。每一联末尾一个字,都是“韵”,或称“韵脚”。这首诗第一联末尾是“依”字,于是以下三联末尾一字就必须用与“依”字同韵的字。
按照这样的规律结构起来的诗,称为“五言四韵诗”。后来称为“五言律诗”,简称“五律”。我国古代诗歌,最早的是《诗经》里的三百零五篇四言诗。其后有了以六言句为主的《楚辞》。汉、魏、南北朝诗才以五言为主。这些古诗,都不在声、韵、词性、句法上作出严格的规律。因此,在唐代以前,还没有“律诗”。王绩这一首诗是最早的唐代律诗,但在王绩的时候,“律诗”这个名词还没有出现,故一般仅称为“五言四韵”。
这首诗是作者在故乡北山下东皋上傍晚眺望时有感而作。东皋,即东边的高原。第一句“东皋薄暮望”,说明了诗题。地:东皋,时:薄暮,事:望,全都交代了。这种表现方法,叫做“点题”。五、七言律诗的第一句,或第一、二句,通常都得先点题。第二句是说出作者在眺望时的思想感情。如果从字面上讲,对照上一句,他是觉得转来转去没有一个可以依靠的地方。但这样讲却是死讲、实讲。他并不是找不到一个可以依靠的地方,而是找不到一个可以依靠的人物。一方面是没有赏识他的人,另一方面是没有他看得中愿意去投奔的人。因此,在社会上“徙倚”多年,竞没有归宿之处。这是活讲、虚讲。诗和散文句法的不同,就在这里。在散文里,“徙倚”必须说出在什么地方,“依”必须说出依的是什么对象:是人物还是树木或山石。象这一句诗,不增加几个名词是无法译成散文句的。因此,散文句子绝大多数不会有双关意义。
第三、四句,即第二联,描写眺望到的景色。每一株树都显出了秋色(树叶的黄色),每一个山头都只有斜阳照着。这也还是按字面死讲,而其含蓄的意义却是:眼前所见尽是衰败没落的现象,不是我所愿依靠的和平、繁荣的世界。
第三联是描写眺望到的人物。牧人赶着牛羊,骑马的猎人带了许多狩获物,都回家去了。第四联就接上去说;这些牧人和猎户,他们看看我,我也看看他们,彼此都没有相识的人。于是作者写出了第八句。在一个衰败没落的环境中,又遇不到一个相识的人,便只好放声高歌,想念起古代两个隐居山中、采野菜过活的伯夷、叔齐了。
一首律诗,主题思想的表现,都在第一联和第四联。第二联和第三联,虽然必须做对句,较为难做,但在表达全诗思想内容,并不占重要的地位。我们如果把这首诗的第二、三联删去,留下第一,四联,这首诗的思想内容并没有重要的缺少:
东皋薄暮望,徒倚欲何依。
相顾无相识,长歌怀采薇。
你看,这样一写,第二句的“依”字更清楚了。作者所要依的肯定是人,而不是树木山石。
学习一切文学作品,必须先了解这个作品及其作者的时代背景。在我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传统上,有一个成语,也可以说是文学批评术语,叫作“知人论世”。要了解一个作家之为人,必须先讨论一下他所处的是个什么时世。但是,了解一个作家的时代背景较为容易,这个作家的传记资料愈多,我们对他的“知人论世”工作便愈容易做。至于一篇作品的时代背景,就较难了解。因为一个人的时代背景是几十年间的事,一篇作品的时代背景,可能只是作者的一小段生活环境。对于一个诗人,我们要知道他的某一首诗是在什么情况下写的,除非作者本人在诗题或诗序中自己交代明白,否则就很不容易明确知道。
王绩身经隋唐二代,对于他这首待,似乎必须失知道它是在什么时候写的,才能了解它针对的是些什么。著《唐诗解》的明人唐汝询说:“此感隋之将亡也。”这样,他是把此诗的写作时间定在隋亡以前。这样,第二联就成为比喻隋代政治的没落了。清人吴昌祺对唐汝询的意见,表示异议,在《删订唐诗解》中加上一个批语:“然王尝仕唐,则通首只无相识之意。”唐汝询以为王绩感隋之将亡,因而,为了忠于隋代,有效法伯夷、叔齐,归隐首阳山之志。吴昌祺提醒了一句,王绩也做过唐代的官,不能把这首诗理解为有隐居不仕之志。唐汝询以“长歌怀采薇”为这首诗的主题思想,吴昌祺则以为诗的重点在“相顾无相识”,“徙倚欲何依”。何文焕在顾安的《唐律消夏录》中增批了一句“王无功,隋之遗老也。‘欲何依’,‘怀采藏’,可以见其志矣。”这样讲,就把诗的写作时间定在隋亡以后,而以为王绩是隋之遗老,所以赋诗见面表示要做一个“不食周粟”的隐士。
许多著名的唐诗,历代以来,曾经许多人评讲。同一首诗,往往有很多不同的理解。关于王绩这首诗,我选取了三家的评论,以为代表。何文焕的讲法,显然不是可取的,因为王绩在唐代做过门下省待诏、太乐署丞,虽然没有几年,已不能说他是隋代的遗老。至于他在贞观初年,已经告老回乡,这里很可能有政治上的利害得失,史书没有记录,我们就无从知道。
我以为这首诗很可能作于隋代政权将亡或已亡之时。但王绩并不效忠于这个一片秋色和残阳的政权。他的“长歌怀采薇”是为了“徙倚欲何依”,是为了个人的没有出路。待到唐皇朝建立,李渊征集隋代职官,王绩就应征到长安出仕,可见他并不以遗老自居。
我这样讲,完全是“以意逆志”,没有文献可以参证。但是恐怕也只有这样讲法,才比较讲得通。
一九七八年一月四日
树树皆秋色,山山惟落晖。
牧人驱犊返,猎马带禽归。
相顾无相识,长歌怀采薇。
王绩,字无功,绛州龙门(今山西龙门)人。隋大业末,官为秘书正字。因不愿在京朝任职,就出去做六合县丞。天天饮酒,不理政事。不久,义兵四起,天下大乱,隋朝政权,有即将崩溃之势。他就托病辞官,回到家乡。李唐政权建立后,武德年间,征集隋朝职官,以备选任。王绩还应征到长安,任门下省待诏。贞观初年,因病告退,仍回故乡,隐居于北山东皋,自号东皋子。王绩与其兄王通,都不热中于仕宦。王通隐居讲学,为河汾之间儒学宗师,著有《文中子》。王绩以诗赋著名,其文集名《东皋子集》。
隋文帝杨坚结束了南北朝对峙的历史,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上统一了中国。南北两个文化系统,逐渐趋于融合。但是杨坚的政权,被他的荒淫无度的儿子杨广断送了。统一的新文化.没有来得及发展。在初唐的几十年间,唐代文化,特别是文学,基本上是隋代的继续。
王绩生于隋末唐初,文学史家一般把他列为最早的唐代诗人。我们现在选讲唐诗,也就从王绩开始。《野望》是王绩的著名诗作。这首诗一共八句,每句五字。古人称一个字为一“言”,故每句五字的诗,称为五言诗。第三句和第四句词性一致,句法结构相同。第五句和第六句也是词性一致,也是句法结构相同。这样形式的结构,称为“对字”,或称“对偶”、“对仗”。每二句称为一联。词性一致的对句,如“树树皆秋色,山山惟落晖”,称为“对联”。上、下二句不对的,如“东皋薄暮望,徙倚欲何依”,和“相顾无相识,长歌怀采薇”,都称为“散联”。每一联末尾一个字,都是“韵”,或称“韵脚”。这首诗第一联末尾是“依”字,于是以下三联末尾一字就必须用与“依”字同韵的字。
按照这样的规律结构起来的诗,称为“五言四韵诗”。后来称为“五言律诗”,简称“五律”。我国古代诗歌,最早的是《诗经》里的三百零五篇四言诗。其后有了以六言句为主的《楚辞》。汉、魏、南北朝诗才以五言为主。这些古诗,都不在声、韵、词性、句法上作出严格的规律。因此,在唐代以前,还没有“律诗”。王绩这一首诗是最早的唐代律诗,但在王绩的时候,“律诗”这个名词还没有出现,故一般仅称为“五言四韵”。
这首诗是作者在故乡北山下东皋上傍晚眺望时有感而作。东皋,即东边的高原。第一句“东皋薄暮望”,说明了诗题。地:东皋,时:薄暮,事:望,全都交代了。这种表现方法,叫做“点题”。五、七言律诗的第一句,或第一、二句,通常都得先点题。第二句是说出作者在眺望时的思想感情。如果从字面上讲,对照上一句,他是觉得转来转去没有一个可以依靠的地方。但这样讲却是死讲、实讲。他并不是找不到一个可以依靠的地方,而是找不到一个可以依靠的人物。一方面是没有赏识他的人,另一方面是没有他看得中愿意去投奔的人。因此,在社会上“徙倚”多年,竞没有归宿之处。这是活讲、虚讲。诗和散文句法的不同,就在这里。在散文里,“徙倚”必须说出在什么地方,“依”必须说出依的是什么对象:是人物还是树木或山石。象这一句诗,不增加几个名词是无法译成散文句的。因此,散文句子绝大多数不会有双关意义。
第三、四句,即第二联,描写眺望到的景色。每一株树都显出了秋色(树叶的黄色),每一个山头都只有斜阳照着。这也还是按字面死讲,而其含蓄的意义却是:眼前所见尽是衰败没落的现象,不是我所愿依靠的和平、繁荣的世界。
第三联是描写眺望到的人物。牧人赶着牛羊,骑马的猎人带了许多狩获物,都回家去了。第四联就接上去说;这些牧人和猎户,他们看看我,我也看看他们,彼此都没有相识的人。于是作者写出了第八句。在一个衰败没落的环境中,又遇不到一个相识的人,便只好放声高歌,想念起古代两个隐居山中、采野菜过活的伯夷、叔齐了。
一首律诗,主题思想的表现,都在第一联和第四联。第二联和第三联,虽然必须做对句,较为难做,但在表达全诗思想内容,并不占重要的地位。我们如果把这首诗的第二、三联删去,留下第一,四联,这首诗的思想内容并没有重要的缺少:
东皋薄暮望,徒倚欲何依。
相顾无相识,长歌怀采薇。
你看,这样一写,第二句的“依”字更清楚了。作者所要依的肯定是人,而不是树木山石。
学习一切文学作品,必须先了解这个作品及其作者的时代背景。在我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传统上,有一个成语,也可以说是文学批评术语,叫作“知人论世”。要了解一个作家之为人,必须先讨论一下他所处的是个什么时世。但是,了解一个作家的时代背景较为容易,这个作家的传记资料愈多,我们对他的“知人论世”工作便愈容易做。至于一篇作品的时代背景,就较难了解。因为一个人的时代背景是几十年间的事,一篇作品的时代背景,可能只是作者的一小段生活环境。对于一个诗人,我们要知道他的某一首诗是在什么情况下写的,除非作者本人在诗题或诗序中自己交代明白,否则就很不容易明确知道。
王绩身经隋唐二代,对于他这首待,似乎必须失知道它是在什么时候写的,才能了解它针对的是些什么。著《唐诗解》的明人唐汝询说:“此感隋之将亡也。”这样,他是把此诗的写作时间定在隋亡以前。这样,第二联就成为比喻隋代政治的没落了。清人吴昌祺对唐汝询的意见,表示异议,在《删订唐诗解》中加上一个批语:“然王尝仕唐,则通首只无相识之意。”唐汝询以为王绩感隋之将亡,因而,为了忠于隋代,有效法伯夷、叔齐,归隐首阳山之志。吴昌祺提醒了一句,王绩也做过唐代的官,不能把这首诗理解为有隐居不仕之志。唐汝询以“长歌怀采薇”为这首诗的主题思想,吴昌祺则以为诗的重点在“相顾无相识”,“徙倚欲何依”。何文焕在顾安的《唐律消夏录》中增批了一句“王无功,隋之遗老也。‘欲何依’,‘怀采藏’,可以见其志矣。”这样讲,就把诗的写作时间定在隋亡以后,而以为王绩是隋之遗老,所以赋诗见面表示要做一个“不食周粟”的隐士。
许多著名的唐诗,历代以来,曾经许多人评讲。同一首诗,往往有很多不同的理解。关于王绩这首诗,我选取了三家的评论,以为代表。何文焕的讲法,显然不是可取的,因为王绩在唐代做过门下省待诏、太乐署丞,虽然没有几年,已不能说他是隋代的遗老。至于他在贞观初年,已经告老回乡,这里很可能有政治上的利害得失,史书没有记录,我们就无从知道。
我以为这首诗很可能作于隋代政权将亡或已亡之时。但王绩并不效忠于这个一片秋色和残阳的政权。他的“长歌怀采薇”是为了“徙倚欲何依”,是为了个人的没有出路。待到唐皇朝建立,李渊征集隋代职官,王绩就应征到长安出仕,可见他并不以遗老自居。
我这样讲,完全是“以意逆志”,没有文献可以参证。但是恐怕也只有这样讲法,才比较讲得通。
一九七八年一月四日
王勃:杜少府之任蜀州
城阙辅三秦,风烟望五津。
与君离别意,同是宦游人。
海内存知己,天涯若比邻。
无为在歧路,儿女共沾巾。
现在再讲一首五言律诗,一则因为它也是初唐名作,二则借此补充讲一点五言律诗的艺术技巧。
作者王勃,字子安,是文中子王通的孙子,东皋子王绩的侄孙。他从小就能作诗赋,应进士举及第,还不到二十岁。但他恃才傲物,常常因文章得罪人。旅居剑南(四川),多年没有事做。好不容易补上了虢州参军,不久,又因事罢官。连累到他父亲福畴,也降官去做交阯县令。他到交阯去省亲,在渡海时溺水而死,只有二十八岁。他的诗文集原有三十卷,大约作品不少,但现在只存诗八十馀首。被选在《古文观止》里的《滕王阁序》,是他最著名的作品。
这首诗的题目,在有些选本中题为《送杜少府之任蜀州》,这就更明白了。有一位姓杜的朋友到四川去做某县县尉,作者就写此诗送行。唐代的官制,一个县的行政长官称为“令”,县令以下有一名“丞”,处理文事,有一名“尉”,处理武事。文丞武尉,是协助县令的官职。文人书简来往,或者在公文上,常用“明府”为县令的尊称或代用词,县丞则称为“赞府”,县尉则称为“少府”。这些名词,在唐诗题目中经常见到。现在诗题称“杜少府”,可知他是去就任县尉。
蜀州即蜀郡。成都地区,从汉至隋,均为蜀郡。唐初改郡为州,故王勃改称蜀州。但当时成都地区已改名为益州,不称蜀州。故王勃虽然改郡字为州字,仍是用的古地名。向来注家均引《旧唐书·地理志》所载“蜀州”作注。这个蜀州是武后垂拱二年(公元六八六年)从益州分出四县设置的,其时王勃已死,他不可能知道有这个蜀州。
此诗第一联是点明题目。上句“城阙辅三秦”是说蜀州是物产富饶的地方,那里每一个城市都对三秦有辅佐之功。下句的“五津”是蜀州的代用词。“风烟”即风景。此句说自己遥望蜀州风景。上句是对杜少府说的:你并不是到一个边荒的地方去作官,而是到一个对京都有重要贡献的地方去作官。下句是从送行者的立场说:你走了,我只能遥望那边的风景。
送人远行,就要作诗,这是唐代知识分子的风俗。一部《全唐诗》,送行赠别的诗占了很大的百分比。这类诗的作法,多数是用第一联两句来点题,照顾到主客双方。例如崔曙《送薛据之宋州》诗云:“无媒嗟失路,有道亦乘流。”第一句说自己,因为无人介绍,至今失业。第二句说薛据:你是有道之士,可也得乘舟东去谋食。郎士元《送孙侍郎往容府宣慰》诗第一联云:“春原独立望湘川,击隼南飞上楚天。”也是第一句说自己:在春原上独立遥望你去的湘水流域。第二句恭维孙侍郎此行是像鹰隼那样高飞上楚天。卢照邻《送郑司仓入蜀》诗起二句云:“离人丹水北,游客锦城东。”用“离人”、“游客”,点明题目中“送”字。用“丹水”、“锦城”,点明“蜀”字。王勃此诗,也用同样方法,但他组织得更均衡。上句表达了杜少府、蜀州和长安的关系,下句表达了作者、送行者与蜀州的关系。
“城阙辅三秦”这句诗历来有不同的讲法。多数人以为“城阙”指京都长安。如果依句子结构讲,这一句就应当讲作“长安辅助三秦”。但是,从事理上想一想,这样讲是讲不通的。北京与郊县的关系,总是郊县辅助北京,不能说是北京辅助郊县。于是一般人都讲作“长安以三秦为辅”,使这个“辅”字成为被动词。即使说这样讲对了,这句诗和题目又有什么关系呢?
于是有人觉得“城阙”应当是指蜀州的。可是,一看到“阙”字,就想到宫阙,蜀州既非京都,怎么会有“城阙”呢?于是吴昌祺说:“蜀称城阙,以昭烈也。”他是从历史上去求解释。巴蜀是刘备建国之地,成都是蜀都,所以也可以用“城阙”。
按“城阙”二字,早已见于《诗经》。“佻兮达兮,在城阙兮”,这是《郑风·子衿》的诗句。孔颖达注解说:“谓城上别有高阙,非宫阙也。”他早已怕读者误解为京城的宫阙,所以说得很明白,城阙是有高楼的城墙。只要是州郡大城市,城头上都有高楼,都可以称城阙。王勃和孔颖达同时。他当然把“城阙”作一般性的名词用,并不特指京都。再看唐人诗中用“城阙”的,固然有指长安的,也有不指长安的。李颀《望秦川》诗云:“远近山河净,逶迤城阙重。”这“城阙”是多数。韩愈《题楚庄王庙》诗云:“丘坟满目衣冠尽,城阙连云草树荒。”韦应物《澧上寄幼遐》诗云;“寂寞到城阙,惆怅返柴荆。”这几个“城阏”,显然不是指长安。
巴蜀为富饶之地,自从开通了秦、蜀之间的栈道,秦中人民的生活资料,一向靠巴蜀支援。从汉武帝以来,论秦、蜀经济关系的文献,都是这样说的。与王勃同时的陈子昂也说:“蜀为西南一都会,国家之宝库,天下珍货聚出其中,又人富粟多,顺江而下,可以兼济中国。”(《谏讨生羌书》)后来杜甫也说:“蜀之土地膏腴,物产繁富,足以供王命也。”(《论巴蜀安危表》)由此可见王勃送杜少府去蜀州,第一句就赞扬蜀中城市是三秦的支援者,这也是代表了一般的观点。可是现在还有许多人注唐诗,坚持“城阙”是指长安,于是把这句诗讲得很不合理。我感到不能不在这里详细辩论一番。
“风烟望五津”句历来注释都以为“五津”是说蜀州地势险恶,“风烟”是形容远望不清。唐汝询释云:“蜀州虽有五津之险,而实为三秦之辅,故我望彼之风烟,而知今之离别,仍为宦游,非暌离也。”他这样讲法,可知他对于“风烟”一句,实在没有明确理解,以致下文愈讲愈错。
我说“风烟”即“风景”,这也是新近才恍然大悟的。唐太宗李世民有一篇《感旧赋》,是怀念洛阳而作。有二句云:“地不改其城阙,时无异其风烟。”此处也是以“城阙”对“风烟”,意思就是城阙依然,风景无异。王勃此诗,完全用太宗的对法,可知这个“风烟”应解作“风景”。唐人常常为平仄关系,改变词汇。“景”字仄声,“烟”字平声,在需要用平声的时候,“风景”不妨改为“风烟”。李白《春夜宴桃李园序》有句云:“大块假我以文章,阳春召我以烟景。”这个“烟景”,也就是“风景”。
现在,我们接下去讲第二联。作者说:我和你今天在这里离别,同样是游宦人的情意。离开家乡,到远地去求学,称为“游士”、或“游学”。去做官,称为“游宦”,也称“宦游”。强调游,就用“宦游”;强调宦,就用“游宦”。
第三联大意是:只要四海之内还有一个知己朋友,虽然远隔天涯,也好似近在邻居。这是对杜少府的安慰,同时也有点赞扬。对杜少府来说,你远去蜀中,不要感到寂寞,还有知已朋友在这里,不因距离远而就此疏淡。对自己来说,像杜少府这样的知己朋友,纵然现在远去蜀中,也好像仍在长安时时见面一样。这两句是作者的名句,也是唐诗中数一数二的名句。但这两句并非王勃的创造,他是从曹植的诗“丈夫志四海,万里犹比邻”变化而成,他利用“万里犹比邻”这个概念,配上“海内存知己”,诗意就与曹植不同。后来王建也有两句诗:“长安无旧识,百里是天涯。”这是把王勃的诗意,反过来用。不能不说是偷了王勃的句法。
第四联是紧跟第三联而写的。既然“天涯若比邻”,那么,现在在岔路口分别,大家就不必像小儿女那样哭哭啼啼。诗歌的创作方法,往往用形象性的具体语词来代替抽象概念。人哭了就要用手帕(巾)拭眼泪,于是“沾巾”就可以用来代替哭泣。这种字眼叫做“代词”或“代语”。运用代语对寻找韵脚有很大的方便。
这首诗和王绩的《野望》虽然都是五言律诗,但句法的艺术结构却完全不同。(一)《野望》的第一联是散联,不是对联。《杜少府》的第一联是很工致的对联。这里,我们首先见到律诗的两种句式,即第一联可以是对句,也可以是不对句。(二)《野望》的第二联和第三联是同一类型的对句。“树树”对“山山”,“秋色”对“落晖”,“皆”对“惟”,四声、词性都是对稳的,每一句都是一个完整的句子,表现一个完整的概念。这种对句,每一联上、下两句的思想内容是各自独立,没有联系的。如果看一看《杜少府》的第二,三联,可以发现,每句都不是完整的句子。“与君离别意”,不成为一个完整的概念,必须读了“同是宦游人”才获得一个概念。因此,从语法的角度讲,《野望》的第二、三联是四句,《杜少府》的第二、三联只有二句。这里,我们看到了律诗的两种对句法。《野望》式的对句,称为“正对”。这是刘勰在《文心雕龙》里定下的名词。他举出四种对法,正对是最常用最低级的对法。《杜少府》的对法,宋朝人称为“流水对”,又称“十字格”。因为从字面结构看,它们是一式二句;但从表现的思想内容看,只是不可分开的一个十字句。就像流水一般,剪不断。这种对句,艺木性就较高。
王勃这首诗,两联都用流水对,使读者不觉得它们是对句,只觉得像散文一样流利地抒写赠别的友谊,因而成为千秋名句。
一九七八年一月七日
城阙辅三秦,风烟望五津。
与君离别意,同是宦游人。
海内存知己,天涯若比邻。
无为在歧路,儿女共沾巾。
现在再讲一首五言律诗,一则因为它也是初唐名作,二则借此补充讲一点五言律诗的艺术技巧。
作者王勃,字子安,是文中子王通的孙子,东皋子王绩的侄孙。他从小就能作诗赋,应进士举及第,还不到二十岁。但他恃才傲物,常常因文章得罪人。旅居剑南(四川),多年没有事做。好不容易补上了虢州参军,不久,又因事罢官。连累到他父亲福畴,也降官去做交阯县令。他到交阯去省亲,在渡海时溺水而死,只有二十八岁。他的诗文集原有三十卷,大约作品不少,但现在只存诗八十馀首。被选在《古文观止》里的《滕王阁序》,是他最著名的作品。
这首诗的题目,在有些选本中题为《送杜少府之任蜀州》,这就更明白了。有一位姓杜的朋友到四川去做某县县尉,作者就写此诗送行。唐代的官制,一个县的行政长官称为“令”,县令以下有一名“丞”,处理文事,有一名“尉”,处理武事。文丞武尉,是协助县令的官职。文人书简来往,或者在公文上,常用“明府”为县令的尊称或代用词,县丞则称为“赞府”,县尉则称为“少府”。这些名词,在唐诗题目中经常见到。现在诗题称“杜少府”,可知他是去就任县尉。
蜀州即蜀郡。成都地区,从汉至隋,均为蜀郡。唐初改郡为州,故王勃改称蜀州。但当时成都地区已改名为益州,不称蜀州。故王勃虽然改郡字为州字,仍是用的古地名。向来注家均引《旧唐书·地理志》所载“蜀州”作注。这个蜀州是武后垂拱二年(公元六八六年)从益州分出四县设置的,其时王勃已死,他不可能知道有这个蜀州。
此诗第一联是点明题目。上句“城阙辅三秦”是说蜀州是物产富饶的地方,那里每一个城市都对三秦有辅佐之功。下句的“五津”是蜀州的代用词。“风烟”即风景。此句说自己遥望蜀州风景。上句是对杜少府说的:你并不是到一个边荒的地方去作官,而是到一个对京都有重要贡献的地方去作官。下句是从送行者的立场说:你走了,我只能遥望那边的风景。
送人远行,就要作诗,这是唐代知识分子的风俗。一部《全唐诗》,送行赠别的诗占了很大的百分比。这类诗的作法,多数是用第一联两句来点题,照顾到主客双方。例如崔曙《送薛据之宋州》诗云:“无媒嗟失路,有道亦乘流。”第一句说自己,因为无人介绍,至今失业。第二句说薛据:你是有道之士,可也得乘舟东去谋食。郎士元《送孙侍郎往容府宣慰》诗第一联云:“春原独立望湘川,击隼南飞上楚天。”也是第一句说自己:在春原上独立遥望你去的湘水流域。第二句恭维孙侍郎此行是像鹰隼那样高飞上楚天。卢照邻《送郑司仓入蜀》诗起二句云:“离人丹水北,游客锦城东。”用“离人”、“游客”,点明题目中“送”字。用“丹水”、“锦城”,点明“蜀”字。王勃此诗,也用同样方法,但他组织得更均衡。上句表达了杜少府、蜀州和长安的关系,下句表达了作者、送行者与蜀州的关系。
“城阙辅三秦”这句诗历来有不同的讲法。多数人以为“城阙”指京都长安。如果依句子结构讲,这一句就应当讲作“长安辅助三秦”。但是,从事理上想一想,这样讲是讲不通的。北京与郊县的关系,总是郊县辅助北京,不能说是北京辅助郊县。于是一般人都讲作“长安以三秦为辅”,使这个“辅”字成为被动词。即使说这样讲对了,这句诗和题目又有什么关系呢?
于是有人觉得“城阙”应当是指蜀州的。可是,一看到“阙”字,就想到宫阙,蜀州既非京都,怎么会有“城阙”呢?于是吴昌祺说:“蜀称城阙,以昭烈也。”他是从历史上去求解释。巴蜀是刘备建国之地,成都是蜀都,所以也可以用“城阙”。
按“城阙”二字,早已见于《诗经》。“佻兮达兮,在城阙兮”,这是《郑风·子衿》的诗句。孔颖达注解说:“谓城上别有高阙,非宫阙也。”他早已怕读者误解为京城的宫阙,所以说得很明白,城阙是有高楼的城墙。只要是州郡大城市,城头上都有高楼,都可以称城阙。王勃和孔颖达同时。他当然把“城阙”作一般性的名词用,并不特指京都。再看唐人诗中用“城阙”的,固然有指长安的,也有不指长安的。李颀《望秦川》诗云:“远近山河净,逶迤城阙重。”这“城阙”是多数。韩愈《题楚庄王庙》诗云:“丘坟满目衣冠尽,城阙连云草树荒。”韦应物《澧上寄幼遐》诗云;“寂寞到城阙,惆怅返柴荆。”这几个“城阏”,显然不是指长安。
巴蜀为富饶之地,自从开通了秦、蜀之间的栈道,秦中人民的生活资料,一向靠巴蜀支援。从汉武帝以来,论秦、蜀经济关系的文献,都是这样说的。与王勃同时的陈子昂也说:“蜀为西南一都会,国家之宝库,天下珍货聚出其中,又人富粟多,顺江而下,可以兼济中国。”(《谏讨生羌书》)后来杜甫也说:“蜀之土地膏腴,物产繁富,足以供王命也。”(《论巴蜀安危表》)由此可见王勃送杜少府去蜀州,第一句就赞扬蜀中城市是三秦的支援者,这也是代表了一般的观点。可是现在还有许多人注唐诗,坚持“城阙”是指长安,于是把这句诗讲得很不合理。我感到不能不在这里详细辩论一番。
“风烟望五津”句历来注释都以为“五津”是说蜀州地势险恶,“风烟”是形容远望不清。唐汝询释云:“蜀州虽有五津之险,而实为三秦之辅,故我望彼之风烟,而知今之离别,仍为宦游,非暌离也。”他这样讲法,可知他对于“风烟”一句,实在没有明确理解,以致下文愈讲愈错。
我说“风烟”即“风景”,这也是新近才恍然大悟的。唐太宗李世民有一篇《感旧赋》,是怀念洛阳而作。有二句云:“地不改其城阙,时无异其风烟。”此处也是以“城阙”对“风烟”,意思就是城阙依然,风景无异。王勃此诗,完全用太宗的对法,可知这个“风烟”应解作“风景”。唐人常常为平仄关系,改变词汇。“景”字仄声,“烟”字平声,在需要用平声的时候,“风景”不妨改为“风烟”。李白《春夜宴桃李园序》有句云:“大块假我以文章,阳春召我以烟景。”这个“烟景”,也就是“风景”。
现在,我们接下去讲第二联。作者说:我和你今天在这里离别,同样是游宦人的情意。离开家乡,到远地去求学,称为“游士”、或“游学”。去做官,称为“游宦”,也称“宦游”。强调游,就用“宦游”;强调宦,就用“游宦”。
第三联大意是:只要四海之内还有一个知己朋友,虽然远隔天涯,也好似近在邻居。这是对杜少府的安慰,同时也有点赞扬。对杜少府来说,你远去蜀中,不要感到寂寞,还有知已朋友在这里,不因距离远而就此疏淡。对自己来说,像杜少府这样的知己朋友,纵然现在远去蜀中,也好像仍在长安时时见面一样。这两句是作者的名句,也是唐诗中数一数二的名句。但这两句并非王勃的创造,他是从曹植的诗“丈夫志四海,万里犹比邻”变化而成,他利用“万里犹比邻”这个概念,配上“海内存知己”,诗意就与曹植不同。后来王建也有两句诗:“长安无旧识,百里是天涯。”这是把王勃的诗意,反过来用。不能不说是偷了王勃的句法。
第四联是紧跟第三联而写的。既然“天涯若比邻”,那么,现在在岔路口分别,大家就不必像小儿女那样哭哭啼啼。诗歌的创作方法,往往用形象性的具体语词来代替抽象概念。人哭了就要用手帕(巾)拭眼泪,于是“沾巾”就可以用来代替哭泣。这种字眼叫做“代词”或“代语”。运用代语对寻找韵脚有很大的方便。
这首诗和王绩的《野望》虽然都是五言律诗,但句法的艺术结构却完全不同。(一)《野望》的第一联是散联,不是对联。《杜少府》的第一联是很工致的对联。这里,我们首先见到律诗的两种句式,即第一联可以是对句,也可以是不对句。(二)《野望》的第二联和第三联是同一类型的对句。“树树”对“山山”,“秋色”对“落晖”,“皆”对“惟”,四声、词性都是对稳的,每一句都是一个完整的句子,表现一个完整的概念。这种对句,每一联上、下两句的思想内容是各自独立,没有联系的。如果看一看《杜少府》的第二,三联,可以发现,每句都不是完整的句子。“与君离别意”,不成为一个完整的概念,必须读了“同是宦游人”才获得一个概念。因此,从语法的角度讲,《野望》的第二、三联是四句,《杜少府》的第二、三联只有二句。这里,我们看到了律诗的两种对句法。《野望》式的对句,称为“正对”。这是刘勰在《文心雕龙》里定下的名词。他举出四种对法,正对是最常用最低级的对法。《杜少府》的对法,宋朝人称为“流水对”,又称“十字格”。因为从字面结构看,它们是一式二句;但从表现的思想内容看,只是不可分开的一个十字句。就像流水一般,剪不断。这种对句,艺木性就较高。
王勃这首诗,两联都用流水对,使读者不觉得它们是对句,只觉得像散文一样流利地抒写赠别的友谊,因而成为千秋名句。
一九七八年一月七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