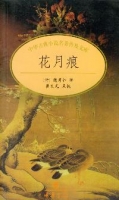情之所钟,端在我辈。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妇、朋友,性也;情字不足以尽之。然自古忠孝节义,有漠然寡情之人乎?自习俗浇薄,用情不能专一,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妇、朋友之间,且相率而为伪,何况其他!乾坤清气间留一二情种,上既不能策名于朝,下又不获食力于家,徒抱一往情深之致,奔走天涯。所闻之事,皆非其心所愿闻,而又不能不闻;所见之人,皆非其心所愿见,而又不能不见,恶乎用其情!
请问看官:渠是情种,砉然坠地时便带有此一点情根,如今要向何处发泄呢?吟风啸月,好景难常;玩水游山,劳人易倦。万不得已而寄其情于名花,万不得已而寄其情于时鸟。窗明几净,得一适情之物而情注之;酒阑灯灺,见一多情之人而情更注之。这段话从那里说起?
因为敝乡有一学究先生,姓虞,号耕心,听小子这般说,便拂然道:“人生有情,当用于正。陶靖节《闲情》一赋,尚贻物议,若舞社歌扇,转瞬皆非,红粉青楼,当场即幻,还讲什么情呢!我们原不必做理学,但生今之世,做今之人,读书是为着科名,谋生是为着妻子。你看那一班潦倒名士,有些子聪明,偏做出怪怪奇奇的事,动人耳根;又做出落落拓拓的样,搭他架子。更有那放荡不羁,傲睨一切,偏低首下心作儿女子态,留恋勾栏中人,——你想,他们有几个梁夫人能识蕲王?有几个关盼盼能殉尚书?大约此等行乐去处,只好逢场作戏,如浮云在空,今日到这里,明日到那里,说说笑笑,都无妨碍,只不要拖泥带水,纠缠不清才好呢。你说什么情种,又是什么情根,我便情田也要踏破,何从留点根,留点种呢!”小子笑道:“先生自知甚明,教人也还踏实,只是将‘情’字径行抹煞!试想:枯木逢春,萌芽便发;生公说法,顽石点头。无论是何等样人,比木石自然不同,如何把人当个登场傀儡?古人力辨‘情’、‘淫’二字,如径渭分明,先生将情田踏破,情种情根一齐除个干净,先生要行什么乐呢?小子不敢说,求先生指教罢!”
学究勃然怒道:“你讲什么话!先王‘人情以为田’,这‘情’字你竟认作男女私情看么?”小子“嗤”的一笑,道:“先生,你怎的不记得上文有‘饮食男女,人之大欲存焉’一句呢!大抵人之良心,其发见最真者,莫如男女分上。故《大学》言诚意,必例之于‘好好色’;《孟子》言舜之孝,必验之于‘慕少艾’。小子南边人,南边有个乐部,生用真男,旦用真女,燃椽烛,铺红氍毹,演唱《醒妓》、《偷诗》等剧,神情意态,比寻常空中摹拟,强有十倍。今人一生,将真面目藏过,拿一副面具套上,外则当场酬酢,内则迩室周旋,即使分若君臣,恩若父子,亲若兄弟,爱若夫妇,谊若朋友,亦只是此一副面具,再无第二副更换。人心如此,世道如此,可惧可忧!读书人做秀才时,三分中却有一分真面目,自登甲科,人仕版,蛇神牛鬼,麇至沓来。”
看官听着:小子说过“今人只是一副面具”,如何又说出许多面目来?须知喜怒威福,十万副面具只是一副铜面具也。然则生今之世,做今之人,真面目如何行得去呢!你看真面目者,其身历坎坷,不一而足。即如先生所说那一班放荡不羁之士,渠起先何曾不自检束,读书想为传人,做官想为名宦?奈心方不圆,肠直不曲,眼高不低,坐此文章不中有司绳尺,言语直触当事逆鳞。又耕无百亩之田,隐元一椽之宅,俯仰求人,浮沈终老,横遭白眼,坐团青毡。不想寻常歌伎中,转有窥其风格倾慕之者,怜其沦落系恋之者,一夕之盟,终身不改。幸而为比翼之鹣,诏于朝,荣于室,盘根错节,脍炙人口;不幸而为分飞之燕,受谗谤,遭挫折,生离死别,咫尺天涯,赍恨千秋,黄泉相见。三生冤债,虽授首于槀街;一段痴情,早销魂于蓬颗。金焦山下,空传蓬鹤之铭;鹦鹉洲边,谁访玉箭之墓!见者酸鼻,闻者拊心,愚俗无知,转成笑柄。先生,你道小子此一派鬼话,是凭空杜撰的么!
小子寻亲不遇,流落临汾县姑射山中,以樵苏种菜为业,五年前,春冻初融,小子锄地,忽地陷一穴,穴中有一铁匣,内藏书数本。其书名《花月痕》,不著作者姓氏,亦不详年代。小子披览一过,将俟此中人传之。其年夏五,旱魃为虐,赤地千里,小子奉母避灾太原,苦无生计,忽悟天授此书,接济小子衣食。因手抄一遍,日携往茶坊,敲起鼓板,赚钱百文,负米以归,供老母一饱。
书中之是非真假,小子亦不知道。但每日间听小子说书的人,也有笑的,也有哭的,也有叹息的,都说道:“书中韦痴珠、刘秋痕,有真性情;韩荷生、杜采秋、李谡如、李夫人,有真意气。即劣如秃僮,傻如跛婢,戆如屠户,懒如酒徒,淫如碧桃,狠如肇受,亦各有真面目,跃跃纸上。”可见人心不死,臧获亦剥果之可珍;直道在民,屠沽本英雄之小隐。至如老魅焚身,鸡栖同烬;幺魔荡影,兔脱遭擒;鼯鼠善缘,终有技穷之日;猢狲作剧,徒增形秽之羞,又可见天道循环,无往不复。冤有头,债有主,愿大众莫结恶缘;生之日,死之年,即顾影亦惭清夜。
小子尝题其卷首云:
有是必有非,是真还是假。
谁知一片心质之开卷者!
今日天气晴明,诸君闲暇无事,何不往柳巷口一味凉茶肆,听小子讲《花月痕》去也。
其缘起如何,且听下回分解。
请问看官:渠是情种,砉然坠地时便带有此一点情根,如今要向何处发泄呢?吟风啸月,好景难常;玩水游山,劳人易倦。万不得已而寄其情于名花,万不得已而寄其情于时鸟。窗明几净,得一适情之物而情注之;酒阑灯灺,见一多情之人而情更注之。这段话从那里说起?
因为敝乡有一学究先生,姓虞,号耕心,听小子这般说,便拂然道:“人生有情,当用于正。陶靖节《闲情》一赋,尚贻物议,若舞社歌扇,转瞬皆非,红粉青楼,当场即幻,还讲什么情呢!我们原不必做理学,但生今之世,做今之人,读书是为着科名,谋生是为着妻子。你看那一班潦倒名士,有些子聪明,偏做出怪怪奇奇的事,动人耳根;又做出落落拓拓的样,搭他架子。更有那放荡不羁,傲睨一切,偏低首下心作儿女子态,留恋勾栏中人,——你想,他们有几个梁夫人能识蕲王?有几个关盼盼能殉尚书?大约此等行乐去处,只好逢场作戏,如浮云在空,今日到这里,明日到那里,说说笑笑,都无妨碍,只不要拖泥带水,纠缠不清才好呢。你说什么情种,又是什么情根,我便情田也要踏破,何从留点根,留点种呢!”小子笑道:“先生自知甚明,教人也还踏实,只是将‘情’字径行抹煞!试想:枯木逢春,萌芽便发;生公说法,顽石点头。无论是何等样人,比木石自然不同,如何把人当个登场傀儡?古人力辨‘情’、‘淫’二字,如径渭分明,先生将情田踏破,情种情根一齐除个干净,先生要行什么乐呢?小子不敢说,求先生指教罢!”
学究勃然怒道:“你讲什么话!先王‘人情以为田’,这‘情’字你竟认作男女私情看么?”小子“嗤”的一笑,道:“先生,你怎的不记得上文有‘饮食男女,人之大欲存焉’一句呢!大抵人之良心,其发见最真者,莫如男女分上。故《大学》言诚意,必例之于‘好好色’;《孟子》言舜之孝,必验之于‘慕少艾’。小子南边人,南边有个乐部,生用真男,旦用真女,燃椽烛,铺红氍毹,演唱《醒妓》、《偷诗》等剧,神情意态,比寻常空中摹拟,强有十倍。今人一生,将真面目藏过,拿一副面具套上,外则当场酬酢,内则迩室周旋,即使分若君臣,恩若父子,亲若兄弟,爱若夫妇,谊若朋友,亦只是此一副面具,再无第二副更换。人心如此,世道如此,可惧可忧!读书人做秀才时,三分中却有一分真面目,自登甲科,人仕版,蛇神牛鬼,麇至沓来。”
看官听着:小子说过“今人只是一副面具”,如何又说出许多面目来?须知喜怒威福,十万副面具只是一副铜面具也。然则生今之世,做今之人,真面目如何行得去呢!你看真面目者,其身历坎坷,不一而足。即如先生所说那一班放荡不羁之士,渠起先何曾不自检束,读书想为传人,做官想为名宦?奈心方不圆,肠直不曲,眼高不低,坐此文章不中有司绳尺,言语直触当事逆鳞。又耕无百亩之田,隐元一椽之宅,俯仰求人,浮沈终老,横遭白眼,坐团青毡。不想寻常歌伎中,转有窥其风格倾慕之者,怜其沦落系恋之者,一夕之盟,终身不改。幸而为比翼之鹣,诏于朝,荣于室,盘根错节,脍炙人口;不幸而为分飞之燕,受谗谤,遭挫折,生离死别,咫尺天涯,赍恨千秋,黄泉相见。三生冤债,虽授首于槀街;一段痴情,早销魂于蓬颗。金焦山下,空传蓬鹤之铭;鹦鹉洲边,谁访玉箭之墓!见者酸鼻,闻者拊心,愚俗无知,转成笑柄。先生,你道小子此一派鬼话,是凭空杜撰的么!
小子寻亲不遇,流落临汾县姑射山中,以樵苏种菜为业,五年前,春冻初融,小子锄地,忽地陷一穴,穴中有一铁匣,内藏书数本。其书名《花月痕》,不著作者姓氏,亦不详年代。小子披览一过,将俟此中人传之。其年夏五,旱魃为虐,赤地千里,小子奉母避灾太原,苦无生计,忽悟天授此书,接济小子衣食。因手抄一遍,日携往茶坊,敲起鼓板,赚钱百文,负米以归,供老母一饱。
书中之是非真假,小子亦不知道。但每日间听小子说书的人,也有笑的,也有哭的,也有叹息的,都说道:“书中韦痴珠、刘秋痕,有真性情;韩荷生、杜采秋、李谡如、李夫人,有真意气。即劣如秃僮,傻如跛婢,戆如屠户,懒如酒徒,淫如碧桃,狠如肇受,亦各有真面目,跃跃纸上。”可见人心不死,臧获亦剥果之可珍;直道在民,屠沽本英雄之小隐。至如老魅焚身,鸡栖同烬;幺魔荡影,兔脱遭擒;鼯鼠善缘,终有技穷之日;猢狲作剧,徒增形秽之羞,又可见天道循环,无往不复。冤有头,债有主,愿大众莫结恶缘;生之日,死之年,即顾影亦惭清夜。
小子尝题其卷首云:
有是必有非,是真还是假。
谁知一片心质之开卷者!
今日天气晴明,诸君闲暇无事,何不往柳巷口一味凉茶肆,听小子讲《花月痕》去也。
其缘起如何,且听下回分解。
京师繁华靡丽,甲于天下。独城之东南有一锦秋墩,上有亭,名陶然亭,百年前水部郎江藻所建。四围远眺,数十里城池村落,尽在目前,别有潇洒出尘之致。亭左近花神庙,绵竹为墙,亦有小亭。亭外孤坟三尺,春时葬花于此,或传某校书埋玉之所。那年春闱榜后,朝议举行鸿词科,因此各道公车,迟留观望,不尽出都。
此书上回所表韦痴珠,系东越人,自十九岁领乡荐后,游历大江南北,酉登太华,东上泰山。祖士稚气概激昂,桓子野性情凄恻,痴珠兼而有之。文章憎命,对策既摈于主司,上书复伤乎执政。此番召试词科,因偕窗友万庶常;同寓圆通观中,托词病暑,礼俗土概屏不见。左图右史,朝夕自娱。
光阴易度,忽忽秋深,乡思羁愁,百无聊赖。忽想起陶然亭地高境旷,可以排拓胸襟,也不招庶常同往,只带随身小童,名唤秃头,雇车出城,一径往锦秋墩来。遥望残柳垂丝,寒芦飘絮,一路倒也夷然。不一会,到了墩前,见有五六辆高鞍车,歇在庙门左右。秃头已经下车,取过脚踏,痴珠便慢慢下车来,步行上墩。
刚到花神庙门口,迎面走出一群人,当头一个美少年,服饰甚都,面若冠玉,唇若涂朱,目光眉彩,奕奕动人。看他年纪,不过二十余岁。随后两人,都有三十许,也自举止娴雅。前后四个相公跟着,说说笑笑。又有一个小僮,捧着拜匣。痴珠偕秃头闪过一边,举目瞧那少年,那位少年也将痴珠望了一望,向前去了。
痴珠直等那一群人都出了门,然后缓步进得门来。白云锁径,黄叶堆阶,便由曲栏走上。见殿壁左厢,墨沈淋漓,一笔苏字草书,写了一首七律。便念道:
“云阴瑟瑟傍高城,闲叩禅扉信步行。
水近万芦吹絮乱,天空一雁比人轻。
疏钟响似惊霜早,晚市尘多匝地生。
寂寞独怜荒冢在,埋香埋玉总多情!”
痴珠看了一遍,讶道:“这首诗高华清爽,必是起先出门那位少年题的。”再看落款,是“富川荷生”,也不知其姓名。正自呆想,只见一个沙弥从殿后走出来。
痴珠因向前相见,随问他:“可认得题诗这人?”沙弥道:“这位老爷姓韩,时常来咱们这里逛,陶然亭上也有他题的诗,却不知道官名住宅。”痴珠道:“这首诗好得很,是个才子之笔。你对汝师父讲,千万护惜着,别涂抹了。”沙弥答应了,便随痴珠逦迤上陶然亭来。满壁琳琅,痴珠因欲读荷生的诗,且先看款。忽见左壁七律一首,款书“春日捆芝香、绮云、竹仙、稚霞诸郎,修楔于此。”后面书“荷生醉笔”四字,不禁大笑,便朗吟道:
“旧时烟草旧时楼,又向江亭快楔游。
尘海琴樽销块垒,春城写燕许勾留。
桃花如雪牵归马,湘水连天泛白鸥。
独上锦秋墩上望,萧萧暮雨不胜愁!”
痴珠想道:“此人清狂拔俗,潇洒不羁,亦可概见。惜相逢不相识,负此一段文字缘了!”沉吟良久,向沙弥要了笔砚,填《台城路》词一阕云:
萧萧落叶西风起,几片断云残柳。草没横塘,苔封古刹,才记旧游
携手。不堪回首。想倚马催诗,听莺载酒。转眼凄凉,虚堂独步迟徊
久!何人高吟词畔,吊新碑如玉,孤坟如斗?三尺桐棺,一杯麦饭,
料得芳心不朽。离怀各有。尽泪堕春前,魂销秋后。感慨悲歌,问花神
知否?
自吟一遍,复书款云:“东越痴珠,秋日游锦秋墩,读富川荷生陶然亭花神庙诗,枨触闲情,倚声和之。”写完,便掷笔笑向沙弥道:“韩老爷再来,汝当以我此词质之,休要忘了。”沙弥亦含笑答应,递上茶来。
痴珠兀自踱来踱去,瞧东瞧西。秃头道:“老爷,你看天要下雨,我们回去,路远着哩。”痴珠仰首一看,东北上黑云布满,遂无心久留,急忙下墩,上车而去。这且按下。
却说荷生,这日自锦秋墩进城,已有三下多钟。一路萧萧疏疏,落起细雨来。同行一为谢小林侍御,一为郑仲池太史,侍御因招荷生携四旦小饮顾曲山房。正上灯赌酒,只见青萍回道:“老苍头来接老爷回去,说‘明经略军营招开,送来经略书信,并聘金三百两,现在寓处,候老爷呈缴,且有话面回。’”荷生迟疑道:“明节相去岁挂印时,原欲邀我人幕,我彼时因春闱在迩,婉辞谢去。今有书来,想必还为这事,但教我怎样处呢?”侍御道:“现在词科既阻于时艰,归路又梗于烽火,何不乘此机会出都,未为不可。”一面催跟班上菜。荷生立起身道:“菜已有了。二君偕诸郎多饮数杯,小弟且告辞回去一看。”侍御也不强留,吩咐提灯,送出大门,看过上车;方才进去。
看官听着:这明经略名禄,本是国家勋戚,累世簪缨,年方四十五岁。弓马娴熟,韬略精通,而且下士礼贤,毫无骄奢气习。五年前与韩荷生的老师、三边总制汪鸿猷先生一同出使西域。江总制屡屡言及,生平得意门生惟有荷生一人,文章词赋,虽不过人,而气宇宏深,才识高远。曾在秦王幕府佐治军书,意欲招之幕中,又恐其不受羁束。彼时明经略已存在心中。后来倭寇勾结西域回部作乱,四方刀兵蠢动,民不聊生,江公奉命防海。明公奉命经略西陲。临别时,经略向汪公求荐人才,江公又把荷生说起,经略立时欲聘同行。荷生因要应鸿词科,不肯同往,经略心颇怅怅。不料回部日更猖獗,经略驻兵太原,一面防边,一面调度河南军务,接济两湖、两江、两广各道粮饷,控制西南,出入钱谷,日以亿万计。羽书旁午,所有随带文武及留营差使各官,虽各有所长,却无主持全局器量,因想起荷生是江公赏鉴的,必定不差。近知词科停止,因致书劝驾。
荷生自旧腊入都,迄今已九阅月,润笔之绢,谈墓之金,到手随尽;正苦囊空,得此机缘,亦自愿意,遂定于九月十二日出都。荷生此行,是明经略敦请去的,自然有许多大老官及同年故旧送赆敬、张祖席,自彰义门至声沟桥,车马络绎。那荷生仍是疏疏落落的,带了老苍头贾忠,小童薛青萍,并新收长随索安、翁慎,一路酬应,到得芦沟桥,已是未末申初时候。
刚至旅店,适值门口拥挤不开,将车停住。只见对面店中一小憧伏侍一人上车,衣服虽不十分华美,而英爽之气见于眉宇,且面熟得很,一时却想不起那里见过。正在凝思,谢侍御及一班同乡京官,还有春庆部、联喜部相公们,一齐迎出,便急忙跳下车来。是晚即在行馆畅饮通宵。
次日起身,午后长新店打尖。到得房中,见新涂粉壁上有诗一首,款书“九月十二日,韦痴珠出都,计自丙申,宿此十度矣。感怀得句,不计工拙也。”想道:“这韦痴珠不就是十年前上那《平倭十策》这人么?”因朗诵道:
“残秋倏欲尽,客子苦行役。行行岂得已,万感在心曲!浮云终日
闲。倦鸟不得宿。蓟门烟树多,芦沟水流浊。回首望西山,苍苍耐寒绿。”
看毕,叹一口气,想道:“此诗飘飘欲仙,然抑郁之意,见于言表。才人不遇,千古如斯!”因触起昨日所见的人,“不知是否此君?看他意绪虽甚无聊,气概却还见兀。我这回出都,好像比他强多,其实沦落天涯,依人作计,正复同病相怜也!”兀坐半晌,只见索安回道:“护送营弁请老爷今日尖后换轿。”荷生想了一回,说道:“坐轿甚好,昨天误了半站,今日着他们多备两班夫,赶上正站,汝们迟到都不妨呢。”
看官,你道荷生要赶正站,是何意思?他记起芦沟桥上车那人。是在花神庙门口注意瞧他的,此刻因人想诗,因诗想人,恨不一下问明。岂知痴珠在都日久,资斧告罄,生平又介介不肯丐人;此番出都,因陕西是旧游之地,且与两川田节度公子有同游草堂之约,决计由晋人秦,由秦人蜀。把箱簏书籍,概托万庶常收管,自与秃头带一付铺盖,一领皮袍,自京到陕二十六站,与车夫约定,兼程前进。你道荷生大队人马,那里赶得上他?正是:
大海飘萍,离合无定。
万里比邻,两心相印。
到底荷生、痴珠踪迹若何,且所下回分解。
此书上回所表韦痴珠,系东越人,自十九岁领乡荐后,游历大江南北,酉登太华,东上泰山。祖士稚气概激昂,桓子野性情凄恻,痴珠兼而有之。文章憎命,对策既摈于主司,上书复伤乎执政。此番召试词科,因偕窗友万庶常;同寓圆通观中,托词病暑,礼俗土概屏不见。左图右史,朝夕自娱。
光阴易度,忽忽秋深,乡思羁愁,百无聊赖。忽想起陶然亭地高境旷,可以排拓胸襟,也不招庶常同往,只带随身小童,名唤秃头,雇车出城,一径往锦秋墩来。遥望残柳垂丝,寒芦飘絮,一路倒也夷然。不一会,到了墩前,见有五六辆高鞍车,歇在庙门左右。秃头已经下车,取过脚踏,痴珠便慢慢下车来,步行上墩。
刚到花神庙门口,迎面走出一群人,当头一个美少年,服饰甚都,面若冠玉,唇若涂朱,目光眉彩,奕奕动人。看他年纪,不过二十余岁。随后两人,都有三十许,也自举止娴雅。前后四个相公跟着,说说笑笑。又有一个小僮,捧着拜匣。痴珠偕秃头闪过一边,举目瞧那少年,那位少年也将痴珠望了一望,向前去了。
痴珠直等那一群人都出了门,然后缓步进得门来。白云锁径,黄叶堆阶,便由曲栏走上。见殿壁左厢,墨沈淋漓,一笔苏字草书,写了一首七律。便念道:
“云阴瑟瑟傍高城,闲叩禅扉信步行。
水近万芦吹絮乱,天空一雁比人轻。
疏钟响似惊霜早,晚市尘多匝地生。
寂寞独怜荒冢在,埋香埋玉总多情!”
痴珠看了一遍,讶道:“这首诗高华清爽,必是起先出门那位少年题的。”再看落款,是“富川荷生”,也不知其姓名。正自呆想,只见一个沙弥从殿后走出来。
痴珠因向前相见,随问他:“可认得题诗这人?”沙弥道:“这位老爷姓韩,时常来咱们这里逛,陶然亭上也有他题的诗,却不知道官名住宅。”痴珠道:“这首诗好得很,是个才子之笔。你对汝师父讲,千万护惜着,别涂抹了。”沙弥答应了,便随痴珠逦迤上陶然亭来。满壁琳琅,痴珠因欲读荷生的诗,且先看款。忽见左壁七律一首,款书“春日捆芝香、绮云、竹仙、稚霞诸郎,修楔于此。”后面书“荷生醉笔”四字,不禁大笑,便朗吟道:
“旧时烟草旧时楼,又向江亭快楔游。
尘海琴樽销块垒,春城写燕许勾留。
桃花如雪牵归马,湘水连天泛白鸥。
独上锦秋墩上望,萧萧暮雨不胜愁!”
痴珠想道:“此人清狂拔俗,潇洒不羁,亦可概见。惜相逢不相识,负此一段文字缘了!”沉吟良久,向沙弥要了笔砚,填《台城路》词一阕云:
萧萧落叶西风起,几片断云残柳。草没横塘,苔封古刹,才记旧游
携手。不堪回首。想倚马催诗,听莺载酒。转眼凄凉,虚堂独步迟徊
久!何人高吟词畔,吊新碑如玉,孤坟如斗?三尺桐棺,一杯麦饭,
料得芳心不朽。离怀各有。尽泪堕春前,魂销秋后。感慨悲歌,问花神
知否?
自吟一遍,复书款云:“东越痴珠,秋日游锦秋墩,读富川荷生陶然亭花神庙诗,枨触闲情,倚声和之。”写完,便掷笔笑向沙弥道:“韩老爷再来,汝当以我此词质之,休要忘了。”沙弥亦含笑答应,递上茶来。
痴珠兀自踱来踱去,瞧东瞧西。秃头道:“老爷,你看天要下雨,我们回去,路远着哩。”痴珠仰首一看,东北上黑云布满,遂无心久留,急忙下墩,上车而去。这且按下。
却说荷生,这日自锦秋墩进城,已有三下多钟。一路萧萧疏疏,落起细雨来。同行一为谢小林侍御,一为郑仲池太史,侍御因招荷生携四旦小饮顾曲山房。正上灯赌酒,只见青萍回道:“老苍头来接老爷回去,说‘明经略军营招开,送来经略书信,并聘金三百两,现在寓处,候老爷呈缴,且有话面回。’”荷生迟疑道:“明节相去岁挂印时,原欲邀我人幕,我彼时因春闱在迩,婉辞谢去。今有书来,想必还为这事,但教我怎样处呢?”侍御道:“现在词科既阻于时艰,归路又梗于烽火,何不乘此机会出都,未为不可。”一面催跟班上菜。荷生立起身道:“菜已有了。二君偕诸郎多饮数杯,小弟且告辞回去一看。”侍御也不强留,吩咐提灯,送出大门,看过上车;方才进去。
看官听着:这明经略名禄,本是国家勋戚,累世簪缨,年方四十五岁。弓马娴熟,韬略精通,而且下士礼贤,毫无骄奢气习。五年前与韩荷生的老师、三边总制汪鸿猷先生一同出使西域。江总制屡屡言及,生平得意门生惟有荷生一人,文章词赋,虽不过人,而气宇宏深,才识高远。曾在秦王幕府佐治军书,意欲招之幕中,又恐其不受羁束。彼时明经略已存在心中。后来倭寇勾结西域回部作乱,四方刀兵蠢动,民不聊生,江公奉命防海。明公奉命经略西陲。临别时,经略向汪公求荐人才,江公又把荷生说起,经略立时欲聘同行。荷生因要应鸿词科,不肯同往,经略心颇怅怅。不料回部日更猖獗,经略驻兵太原,一面防边,一面调度河南军务,接济两湖、两江、两广各道粮饷,控制西南,出入钱谷,日以亿万计。羽书旁午,所有随带文武及留营差使各官,虽各有所长,却无主持全局器量,因想起荷生是江公赏鉴的,必定不差。近知词科停止,因致书劝驾。
荷生自旧腊入都,迄今已九阅月,润笔之绢,谈墓之金,到手随尽;正苦囊空,得此机缘,亦自愿意,遂定于九月十二日出都。荷生此行,是明经略敦请去的,自然有许多大老官及同年故旧送赆敬、张祖席,自彰义门至声沟桥,车马络绎。那荷生仍是疏疏落落的,带了老苍头贾忠,小童薛青萍,并新收长随索安、翁慎,一路酬应,到得芦沟桥,已是未末申初时候。
刚至旅店,适值门口拥挤不开,将车停住。只见对面店中一小憧伏侍一人上车,衣服虽不十分华美,而英爽之气见于眉宇,且面熟得很,一时却想不起那里见过。正在凝思,谢侍御及一班同乡京官,还有春庆部、联喜部相公们,一齐迎出,便急忙跳下车来。是晚即在行馆畅饮通宵。
次日起身,午后长新店打尖。到得房中,见新涂粉壁上有诗一首,款书“九月十二日,韦痴珠出都,计自丙申,宿此十度矣。感怀得句,不计工拙也。”想道:“这韦痴珠不就是十年前上那《平倭十策》这人么?”因朗诵道:
“残秋倏欲尽,客子苦行役。行行岂得已,万感在心曲!浮云终日
闲。倦鸟不得宿。蓟门烟树多,芦沟水流浊。回首望西山,苍苍耐寒绿。”
看毕,叹一口气,想道:“此诗飘飘欲仙,然抑郁之意,见于言表。才人不遇,千古如斯!”因触起昨日所见的人,“不知是否此君?看他意绪虽甚无聊,气概却还见兀。我这回出都,好像比他强多,其实沦落天涯,依人作计,正复同病相怜也!”兀坐半晌,只见索安回道:“护送营弁请老爷今日尖后换轿。”荷生想了一回,说道:“坐轿甚好,昨天误了半站,今日着他们多备两班夫,赶上正站,汝们迟到都不妨呢。”
看官,你道荷生要赶正站,是何意思?他记起芦沟桥上车那人。是在花神庙门口注意瞧他的,此刻因人想诗,因诗想人,恨不一下问明。岂知痴珠在都日久,资斧告罄,生平又介介不肯丐人;此番出都,因陕西是旧游之地,且与两川田节度公子有同游草堂之约,决计由晋人秦,由秦人蜀。把箱簏书籍,概托万庶常收管,自与秃头带一付铺盖,一领皮袍,自京到陕二十六站,与车夫约定,兼程前进。你道荷生大队人马,那里赶得上他?正是:
大海飘萍,离合无定。
万里比邻,两心相印。
到底荷生、痴珠踪迹若何,且所下回分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