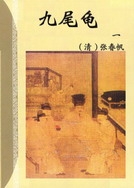第一回谈楔子演说九尾龟访名花调查青阳地
龟有三足,亦有九尾。《尔雅》注云:“南方之龟有九尾,见之者得富贵。”古来麟、凤、龟、龙,列在四灵之内,那乌龟是何等宝贵的东西。降至如今,世风不古,竟把乌龟做了极卑鄙龌龊的混名:妇女或有外遇,群称其夫为“乌龟”。这是个什么讲究呢?大抵也有一个来历,诸公静听,待鄙人慢慢的说来。古从前管仲设女闾三百,以为兵士休宿之所,这便是妓女的滥觞。唐时官妓多隶教坊,设教坊司以管领女乐。那教坊中的人役,皆头裹绿巾,取其象形有似乌龟。列公试想:那乌龟一头两眼,不多是碧绿的么?还有取义的一说,是龟不能交,那雌龟善与蛇交,雄不能禁,因此大凡妇女不端,其夫便有乌龟之号。在下这部小说名叫“九尾龟”,是近来一个富贵达官的小影。这贵官帷薄不修,闹出许多笑话,倒便宜在下,编成了这一部《九尾龟》。主闲话少提,书归正传。且先将一个风流才子类弄登场,好为诸公解秽。正是:知莫把酒杯浇块垒,且将绮梦说莺花。古且说这名士姓章,单名一个莹字,别号秋谷,江南应天府人氏,寄居苏州常熟县。生得白皙丰颐,长身玉立。论他的才调,便是胸罗星斗,倚马万言;论他的胸襟,便是海阔天空,山高月朗;论他的意气,便是蛟龙得雨,鹰隼盘空。这章秋谷有如此的才华意气,却又谈词爽朗,举止从容,真个是美玉良金,隋珠和璧,一望而知他日必为大器的了。斋只是秋谷时运不济,十分偃蹇,十七岁便丁了外艰,三年服阕,便娶了亲。他夫人张氏,身材不长不短,面孔不瘦不肥,虽不是绝世佳人,恰也不十分丑怪,但是性情古执,风趣全无。若在别人,原也不至夫妻反目,无奈秋谷倚着自家万斛清才,一身侠骨,准备着要娶一个才貌双全的绝代名姝,方不辜负他自家才调,娶了这等一个平庸女子,叫他如何不气?气到无可如何之际,便动了个寻花问柳的念头,就借着他事,告禀了太夫人,定了行期,收拾行李,便登舟往苏州进发。知不一日到了苏州,在盘门外一个客栈名叫”佛照楼”的住下。那苏州自从日本通商以来,在盘门城外开了几条马路,设了两家纱厂,那城内仓桥滨的书寓,统通搬到城外来,大菜馆、戏馆、书场,处处俱有,一样的车水马龙,十分热闹。主秋谷落栈之后,歇息了一日,不免往书场、戏馆去涉猎涉猎。坐了几天马车,吃了两回大菜,觉得苏州马路的风景不过如此。与上海大不相同,虽然灯火繁华,却时时露出荒凉景象。日间欢场征逐,自有那一班朋友声应气求,到也并不寂寞,只是到了酒阑人散之时,客舍独居,孤灯相对,你道这样风流人物,怎生消受得来?知一日夜饭后并无应酬,信步出栈望马路走来。见那来往兜圈子的马车上坐的那些倌人,真是杨柳为眉,芙蓉如面。同着客人坐在一车的,更是佯嗔娇笑,慎态动人。只苦的自己初到苏州,并无熟识,只得走到一家书场名叫”余香阁”的,走了进去,拣张桌子泡茶坐下,细细的打量台上倌人。只见左首第三座上坐着一个倌人。年纪约十六七岁,珠光侧聚,珮响流葩,眉锁春山,目澄秋水,那粉颊上晕着两个酒涡,似笑非笑的低头敛手,坐在那里弄衣角儿。秋谷一眼看见,吃了一惊,那双眼睛就如被他勾了去的一般,登时神魂不定起来,便呆呆的看着他。主一会儿,那堂倌在傍凑趣,低低的问秋谷道:“这倌人名叫许宝琴,名气狠大,今年尚止十六岁,唱得好一口京调。老爷可要点他两出?”秋谷不答,只微微的点一点头。堂倌便如飞去取了粉牌过来,并拿一枝笔递给秋谷。秋谷提起笔来,写了两出《朱砂痣》、《琼林宴》的京戏,《卖花球》、《白兰花》的两支小调,顿时喊上台去。原来苏州规矩与上海不同,点戏是当台招呼的。知那倌人听有客人点戏,抬起头来,飘了秋谷一眼,又微笑一笑,只觉媚眼横波、红潮上颊,越显得光容绰约、丰彩飞扬,喜得秋谷色舞眉飞,十分得意。又见一个年轻大姐,手拿着银水烟袋,下来装烟,便问秋谷尊姓,随即应酬了几句,秋谷一一的回答了。知此时许宝琴抱着琵琶,弹了一套开片,背脸儿亢起娇声来,虽不是裂石穿云,却也引商刻羽。唱过一段《朱砂痣》,便把琵琶捺低一调,低低的唱那小调《白兰花》。唱到关情之处,星眸低漾,杏脸微红,把眼波只顾向秋谷溜来,台下看客齐声喝采,到把秋谷弄得不好意思起来。知一会宝琴唱完,对那大姐使一个眼色,那大姐便又下来装了几筒烟,说声:“对勿住,停歇请过来!”便扶着宝琴姗姗而去;临行之际,又向秋谷一笑,方才下楼去了。秋谷急叫堂倌算好了帐,立起身来跟下扶梯,许宝琴还未上轿。立在门口,见秋谷匆匆的下来,含笑招呼道:“章大少,啥勿一淘到倪搭去嗄!”秋谷答应道:“我正要去坐坐,你叫大姐同我去罢。”宝琴便叫那大姐道:“阿仙,格末倪先转去哉,耐同仔章大少要就来格虐。”阿仙答应一声,宝琴便上轿走了。主秋谷同着阿仙一路问答,慢慢的走过了甘棠桥。秋谷早看见了许宝琴的牌子,便进门登楼,相帮叫了一声:“客人上来!”宝琴早换了衣服,接到扶梯边,秋谷携了宝琴的手,同进房来。抬头一看,房间虽然不大,收拾得十分富丽。斋秋谷便在炕上坐下。宝琴敬过瓜子,细细的打量秋谷。正是二月初天气,见他穿着一件白灰色灰鼠皮袍,玄色外国缎草上霜一宇襟坎肩,外罩天青贡缎洋灰鼠马褂,颜色配搭得十分匀衬。长眉凤目。白面丰颐,英爽之气,奕奕逼人,觉得眼中从未见过这样人物,不觉亲热起来,挨着秋谷身旁坐下,应酬了一回。秋谷看他言语之间尚觉有些羞涩,便知初入青楼,不是那林黛玉、翁梅倩一流人物;又见他低颦浅笑,顾盼生怜,不由心花大放,便向宝琴说道:“我今日虽然还是第一次来,竟要在这里请几个客,不知房间可空不空?”宝琴笑道:“只要大少肯照应倪,是再好勿有格事体,倪阿有啥倒勿肯格?”便回头叫房间里娘姨,交代一台菜下去。主秋谷叫拿笔砚过来,写好请客票,发去不多一刻,客人陆续到来。发过局票,秋谷叫起手巾,其时台面已经摆好,大家入座。其中恰有一位客人,是秋谷最敬重的朋友,双姓东方,单名一个瑶字,又号小松。生得仪容俊雅,眉目风流,素有璧人之目,同秋谷意气相投,时常会面的。当下到了席中,一眼先看见了许宝琴,山花宝髻,石竹罗衣,神彩惊鸿,珮环回雪,不觉呆了一呆;又见秋谷与他非常亲热,眉语目成,又如飞燕依人,夭桃初放,便大笑道:“秋谷说苏州地方并无相好,这位贵相知难道是天外飞来的不成?快快实说:是几时做起,为何瞒着我们,是何道理?”秋谷尚未开口,宝琴早已两颊通红,扭转身子,恰好与小松打个照面,更加不好意思,低下头去,口中咕噜道:“耐笃总是实梗瞎三话四,阿要无淘成,倪是要板面孔格。”秋谷听了好笑,便道:“这位方大少,天生的不老成,没有好话说的,你只当他放屁就是了。”又向小松道:“我向来作事从未瞒你,此处我实是今日第一回来,在余香阁点戏之后,钉梢回来的。你不信,只顾问房间里人便了。”那房间里娘姨阿彩、大姐阿仙,一齐说道:“方大少,勿要勿相信,轧实章大少是今朝做起格勒,倪阿肯骗耐嗄。”古小松听了,方才相信,想了一想,又摇摇头道:“我只不信。既然是今天做起,为甚你们先生的神气,倒像与章大少是老相好一样,是何道理?”小松说到此际,早被秋谷捏了一把,使个眼色,小松方才住口。秋谷悄悄埋怨他道:“你取笑也要看地方起的。我今天初次在此请客,你便如此胡言乱语,倘被他真个板起面孔来,你我岂不大家没趣?”小松笑道:“你不要来吓我,我是不怕的,你只好好的叫他转个局,我便不开口了,你肯不肯?”秋谷不觉大笑道:“原来你说了半天,是要割我的靴腰,何不早说,恰要绕着弯儿说呢?”便叫宝琴转过去坐在小松旁边。宝琴抬起头来,着实钉了秋谷一眼,也不言语。秋谷又催一遍,宝琴方才对着小松说道:“方大少,对勿住,倪间搭格规矩:一帮里客人勿做两个格。阿好谢谢耐,勿要扳倪格差头。倪情愿吃子一杯罚酒末哉。”说罢,便叫阿仙取出一只鸡缸杯来,斟了一杯热酒,立起身来,将杯照着小松,竟自吃干了。”小松倒也无可再言。停了一会,忽然笑道:“可恶可恶,我在堂子里头顽儿,总弄你这促掐鬼不过,你总要占个上风,究竟我同你是一样的人,难道我短了什么不成?”说着,又问宝琴道:“你看我们两人,倒底谁的风头好些?”宝琴听小松说得好笑,不免面红一笑,暗中又飞了秋谷一眼,早被对坐的客人名叫孔伯虚的看见,便笑道:“据我看来,秋翁与小翁二人正是工力愁敌,可算得瑜亮并生,一时无两。只是宝琴的意思有些看不上小翁,或是小翁的内才短些,比不上秋翁的精力,那我们外人就无从晓得了。”说得合席大笑起来。恰好各人的局陆续到了,彼此打断了话头。知酒过数巡,小松鼓起兴来,便要摆五十杯的庄。秋谷微笑道:“你这种的酒量也敢摆庄?待我来打坍你的。”于是攘臂而起,正与小松旗鼓相当。旁坐一个姓吴的劝道:“五十杯太多,留几杯等别人来打,你打了二十杯罢!”秋谷依了,便与小松五魁三元的叫了一阵。二十杯庄打完,秋谷自己也输了十五六杯,秋谷慢慢的喝了十杯,还有五杯,便折在一个大玻璃缸里,回过身来递与阿彩,叫他代饮。阿彩刚刚接过,早被宝琴劈手夺来,一口气咕嘟嘟的竟喝了一个干净,面上早红晕起来,放下杯子,那两只秋波水汪汪的更加了几分风韵。小松只顾与别人搳拳,竟不理会。秋谷却是留心的,见他杏眼微饧,桃腮带涩,心上觉得好生怜惜,只是说不出来,便低低的合他说道:“你何苦这样拼命的喝酒,喝醉了便怎样呢?”宝琴微笑不答,秋谷更是魂销。两人相视了好一会,小松的庄早已打完。小松除代酒外,自家也喝了三十余杯,觉得有些沉醉,从腰间掏出一个表来一看,早已指到十二点三刻了,便道:“时候不早了,我们散罢!好等你们两人细细的谈心。”上过干稀饭,各人都掏出两块洋钱放在桌上。秋谷也取出下脚四元,添菜两元,一齐放在台上。相帮进来收拾台面,把洋钱数了一数,七个客人共是十四块,一总二十块洋钱,便高叫一声:“多谢各位大少。”拿了洋钱出房去了。知看官且慢,你道此是什么规矩?原来姑苏书寓规条,大凡请客,须每位客人出台面洋两元,谓之”丢台面。”朋友请吃花酒,若非素日知己,不肯到场。因非但赔贴局钱,又要现丢台面,绝非上海请吃花酒,客人到了就算赏光的风俗。再加上海碰和一概二十元,苏州却无论长三幺二均是八元。以前上海青楼风俗,凡生客进门,倌人必唱京调或小曲一支,名为”堂唱”,恰须现钱开销。现在上海此例已除,姑苏却至今未改,这是苏、沪不同之处,在下预先一一申明,免得要受看官的指摘。主只说客人散后,只有秋谷未曾回去,就在那里借了一夜干铺。名说干铺,只怕明干暗湿也未可知,不在话下。古秋谷睡至晌午,方才起来,洗漱已毕,待要回栈,宝琴叫相帮到正元馆端了一碗一钱六分生炒鸡丝面来,让秋谷吃了;又亲自替秋谷梳了一条辫子,方才放他下楼,又叮嘱他晚上要来。秋谷一一答应了,自回栈去,仍就睡了。约至三下钟,方睡醒起来,随意吃些东西。正待出去,只见许宝琴家的阿仙笑嘻嘻的走进来,道:“章大少,阿是刚刚起来勒?倪先生到书场浪去哉,请耐去点戏。”秋谷也无可不可的,同了阿仙走到余香阁。主正待上楼,只见一顶倌人轿子停在门前,眼前觉得毫光一闪,走出一个倌人来,穿一件黑地银花外国缎灰鼠皮祆,下衬品蓝花缎裤子,玄色缎子弓鞋不到四寸,眉眼虽比许宝琴略逊,那一种的丰姿袅娜,骨格轻盈,却比许宝琴更加妩媚。秋谷立在扶梯边,一直等到他上了楼,目光尚有些定定的,被阿仙从后推了一把,道:“阿是看得头里向有点浑淘淘哉,快点上去哩!”秋谷被他一推,吓了一跳,不觉自己好笑,便走上扶梯,拣一个座位。刚刚坐下,堂倌早送了点戏牌过来,秋谷且不点戏,问着堂倌,那外国缎袄的叫甚名字。堂倌道:“他住在谈瀛里,名叫花云香,还是新近从上海来的,章老爷可要也点他两出?”秋谷要过笔来,便写了《二进宫》、《龙虎斗》、《探寒窑》、《铡美案》四出,都要花云香与许宝琴两人合唱。古堂倌喊了上去,花云香听得分明,回头一看,就是楼梯边的相遇人,不免低头一笑,随叫娘姨下来装烟。许宝琴却着实的钉了秋谷一眼。秋谷虽也看见,并不理会。花云香先了和弦,唱出一段《二进宫》,许宝琴随接唱下去,唱到末尾一句,两人一齐背过脸去,把琵琶放高一调,全用轮指合唱。那一声摇板却唱得顿挫抑扬,十分圆稳,秋谷喝一声采。随后又合唱了一出《铡美案》,许宝琴便先起身走了。只有花云香又独唱一出《探寒窑》,那喉咙愈唱愈高,愈高愈亮,唱到极高之后,一落千丈,就如银瓶落井一般,落到一半却又陡然提起,又如鹤唳入云,声声摇曳,真是珠喉遏月,逸响回风,只听得台下喝采之声轰然不绝。秋谷异常得意。花云香唱完之后,方才立起身来,正走秋谷面前经过,向秋谷点一点头,下楼去了。主秋谷见他走了,无精打采的付了帐,慢慢的下来。才到楼下,不防阿仙候在门口,便一把衣袖拉了秋谷,一直拉到甘棠桥,进门推他上楼。只见宝琴欲笑不笑,一付尴尬面孔,道:“章大少,耐倒有功夫到倪搭来坐坐,啥勿到花云香搭去嗄!”秋谷听了笑道:“你们这班人实在难说话得狠。叫了我来,又叫我到别处去,我就依着你的吩咐,到花家去。”说着,假做回身要走,早被阿仙一把拉住,说道:“耐阿要好意思格!花家里明朝去末哉,倪搭小场化,委屈耐点阿好?”宝琴接口说道:“耐放俚去嗫,看俚阿好意思走出去。”秋谷呵呵笑道:“你们不要我去,也就罢了,何必做出许多生意筋络来。”一面说,一面坐下。主宝琴问道:“阿要吃夜饭哉,就倪搭便饭,去叫仔两样菜阿好?”秋谷正待写菜去叫,只听楼下喊声“请客”。把请客条子递将上来一看,原来是小松请到如意里金黛玉家,上面写着:“容齐坐候入席”,秋谷便立起身来。阿仙便说道:“章大少,阿要带局去罢,省得来叫哉。”秋谷点头道:“也好。”因如意里与许家只隔一桥,便不用轿子,催许宝琴换好了出局衣裳,二人携手出门。知到了金黛玉家,问了房间,恰在楼下。小松早在房门口招呼,进房坐下,满房客人都与秋谷相识,不用套谈。小松见秋谷同着宝琴,便道:“你带局来,倒也简便,可还叫别人么?”秋谷因叫小松代写了一张花云香的局票,一同发去。主少时,大家入席,花云香早姗姗其来,进房含笑叫了一声,便坐在秋谷身后。秋谷不及应酬,便留心打量金黛玉的妆束,只见他:淡扫蛾眉,薄施脂粉,穿一件蜜色皮袄,衬一条妃色裤子。风鬟雾鬓,虽非倾国之姿;素口蛮腰,稳称芳菲之选。那边小松见了花云香,也打量了一会,忽嚷道:“不好了,又被你抢了一个去了!怎么我到处留心,总没有好的;你遇见的,总是好的呢?”秋谷道:“你为什么总是这样脾气?今天是你自己的主人,劝你少说两句罢!”说着,金黛玉起身斟了一巡酒,众客人的局也来了。花云香先唱了一出《取成都》,唱完了,对秋谷说声“献丑”,秋谷说声“辛苦”,便慢慢的谈起来。两人咬着耳朵不知讲些什么。许宝琴却看着冷笑。偶而秋谷回过身来同宝琴说话,宝琴却只是扭过身去,不肯理他。古秋谷正在没做理会处,小松斟了一大杯酒要与秋谷照杯,又笑道:“知己希逢,佳人难得,你快干了这一杯。”秋谷猛然听得,触起他的心事来,长叹一声,举杯一饮而尽,口中高吟道:“此时此景不沉醉,岂待三尺蓬蒿坟。”与小松彼此相对黯然。停了一回,小松方勉强笑道:“我们原是寻乐的,怎么倒寻起烦恼来呢?我与你还是喝酒罢。”秋谷也不回言,自己斟了一杯,又高吟道:“今日少年若长在。古之少年安在哉?”就又干了一杯。主花云香看见秋谷无故不乐,心中觉得十分难过,却又替他不得,便咬着秋谷耳朵道:“耐勿要煞死个吃酒哉,到倪搭去坐歇罢。耐坐仔我个轿子去阿好?”秋谷只点点头。花云香便叫自己的轿子来,亲手将秋谷扶在轿内,自己也立起身来,跟着走出,叫一部东洋车,傍着轿子同走。秋谷也不顾许宝琴,竟自到花家去了,连主人方小松都未招呼。正是:知名士风尘多涕泪,美人香草寄牢骚。古要知后事如何,且听下回分解。斋
龟有三足,亦有九尾。《尔雅》注云:“南方之龟有九尾,见之者得富贵。”古来麟、凤、龟、龙,列在四灵之内,那乌龟是何等宝贵的东西。降至如今,世风不古,竟把乌龟做了极卑鄙龌龊的混名:妇女或有外遇,群称其夫为“乌龟”。这是个什么讲究呢?大抵也有一个来历,诸公静听,待鄙人慢慢的说来。古从前管仲设女闾三百,以为兵士休宿之所,这便是妓女的滥觞。唐时官妓多隶教坊,设教坊司以管领女乐。那教坊中的人役,皆头裹绿巾,取其象形有似乌龟。列公试想:那乌龟一头两眼,不多是碧绿的么?还有取义的一说,是龟不能交,那雌龟善与蛇交,雄不能禁,因此大凡妇女不端,其夫便有乌龟之号。在下这部小说名叫“九尾龟”,是近来一个富贵达官的小影。这贵官帷薄不修,闹出许多笑话,倒便宜在下,编成了这一部《九尾龟》。主闲话少提,书归正传。且先将一个风流才子类弄登场,好为诸公解秽。正是:知莫把酒杯浇块垒,且将绮梦说莺花。古且说这名士姓章,单名一个莹字,别号秋谷,江南应天府人氏,寄居苏州常熟县。生得白皙丰颐,长身玉立。论他的才调,便是胸罗星斗,倚马万言;论他的胸襟,便是海阔天空,山高月朗;论他的意气,便是蛟龙得雨,鹰隼盘空。这章秋谷有如此的才华意气,却又谈词爽朗,举止从容,真个是美玉良金,隋珠和璧,一望而知他日必为大器的了。斋只是秋谷时运不济,十分偃蹇,十七岁便丁了外艰,三年服阕,便娶了亲。他夫人张氏,身材不长不短,面孔不瘦不肥,虽不是绝世佳人,恰也不十分丑怪,但是性情古执,风趣全无。若在别人,原也不至夫妻反目,无奈秋谷倚着自家万斛清才,一身侠骨,准备着要娶一个才貌双全的绝代名姝,方不辜负他自家才调,娶了这等一个平庸女子,叫他如何不气?气到无可如何之际,便动了个寻花问柳的念头,就借着他事,告禀了太夫人,定了行期,收拾行李,便登舟往苏州进发。知不一日到了苏州,在盘门外一个客栈名叫”佛照楼”的住下。那苏州自从日本通商以来,在盘门城外开了几条马路,设了两家纱厂,那城内仓桥滨的书寓,统通搬到城外来,大菜馆、戏馆、书场,处处俱有,一样的车水马龙,十分热闹。主秋谷落栈之后,歇息了一日,不免往书场、戏馆去涉猎涉猎。坐了几天马车,吃了两回大菜,觉得苏州马路的风景不过如此。与上海大不相同,虽然灯火繁华,却时时露出荒凉景象。日间欢场征逐,自有那一班朋友声应气求,到也并不寂寞,只是到了酒阑人散之时,客舍独居,孤灯相对,你道这样风流人物,怎生消受得来?知一日夜饭后并无应酬,信步出栈望马路走来。见那来往兜圈子的马车上坐的那些倌人,真是杨柳为眉,芙蓉如面。同着客人坐在一车的,更是佯嗔娇笑,慎态动人。只苦的自己初到苏州,并无熟识,只得走到一家书场名叫”余香阁”的,走了进去,拣张桌子泡茶坐下,细细的打量台上倌人。只见左首第三座上坐着一个倌人。年纪约十六七岁,珠光侧聚,珮响流葩,眉锁春山,目澄秋水,那粉颊上晕着两个酒涡,似笑非笑的低头敛手,坐在那里弄衣角儿。秋谷一眼看见,吃了一惊,那双眼睛就如被他勾了去的一般,登时神魂不定起来,便呆呆的看着他。主一会儿,那堂倌在傍凑趣,低低的问秋谷道:“这倌人名叫许宝琴,名气狠大,今年尚止十六岁,唱得好一口京调。老爷可要点他两出?”秋谷不答,只微微的点一点头。堂倌便如飞去取了粉牌过来,并拿一枝笔递给秋谷。秋谷提起笔来,写了两出《朱砂痣》、《琼林宴》的京戏,《卖花球》、《白兰花》的两支小调,顿时喊上台去。原来苏州规矩与上海不同,点戏是当台招呼的。知那倌人听有客人点戏,抬起头来,飘了秋谷一眼,又微笑一笑,只觉媚眼横波、红潮上颊,越显得光容绰约、丰彩飞扬,喜得秋谷色舞眉飞,十分得意。又见一个年轻大姐,手拿着银水烟袋,下来装烟,便问秋谷尊姓,随即应酬了几句,秋谷一一的回答了。知此时许宝琴抱着琵琶,弹了一套开片,背脸儿亢起娇声来,虽不是裂石穿云,却也引商刻羽。唱过一段《朱砂痣》,便把琵琶捺低一调,低低的唱那小调《白兰花》。唱到关情之处,星眸低漾,杏脸微红,把眼波只顾向秋谷溜来,台下看客齐声喝采,到把秋谷弄得不好意思起来。知一会宝琴唱完,对那大姐使一个眼色,那大姐便又下来装了几筒烟,说声:“对勿住,停歇请过来!”便扶着宝琴姗姗而去;临行之际,又向秋谷一笑,方才下楼去了。秋谷急叫堂倌算好了帐,立起身来跟下扶梯,许宝琴还未上轿。立在门口,见秋谷匆匆的下来,含笑招呼道:“章大少,啥勿一淘到倪搭去嗄!”秋谷答应道:“我正要去坐坐,你叫大姐同我去罢。”宝琴便叫那大姐道:“阿仙,格末倪先转去哉,耐同仔章大少要就来格虐。”阿仙答应一声,宝琴便上轿走了。主秋谷同着阿仙一路问答,慢慢的走过了甘棠桥。秋谷早看见了许宝琴的牌子,便进门登楼,相帮叫了一声:“客人上来!”宝琴早换了衣服,接到扶梯边,秋谷携了宝琴的手,同进房来。抬头一看,房间虽然不大,收拾得十分富丽。斋秋谷便在炕上坐下。宝琴敬过瓜子,细细的打量秋谷。正是二月初天气,见他穿着一件白灰色灰鼠皮袍,玄色外国缎草上霜一宇襟坎肩,外罩天青贡缎洋灰鼠马褂,颜色配搭得十分匀衬。长眉凤目。白面丰颐,英爽之气,奕奕逼人,觉得眼中从未见过这样人物,不觉亲热起来,挨着秋谷身旁坐下,应酬了一回。秋谷看他言语之间尚觉有些羞涩,便知初入青楼,不是那林黛玉、翁梅倩一流人物;又见他低颦浅笑,顾盼生怜,不由心花大放,便向宝琴说道:“我今日虽然还是第一次来,竟要在这里请几个客,不知房间可空不空?”宝琴笑道:“只要大少肯照应倪,是再好勿有格事体,倪阿有啥倒勿肯格?”便回头叫房间里娘姨,交代一台菜下去。主秋谷叫拿笔砚过来,写好请客票,发去不多一刻,客人陆续到来。发过局票,秋谷叫起手巾,其时台面已经摆好,大家入座。其中恰有一位客人,是秋谷最敬重的朋友,双姓东方,单名一个瑶字,又号小松。生得仪容俊雅,眉目风流,素有璧人之目,同秋谷意气相投,时常会面的。当下到了席中,一眼先看见了许宝琴,山花宝髻,石竹罗衣,神彩惊鸿,珮环回雪,不觉呆了一呆;又见秋谷与他非常亲热,眉语目成,又如飞燕依人,夭桃初放,便大笑道:“秋谷说苏州地方并无相好,这位贵相知难道是天外飞来的不成?快快实说:是几时做起,为何瞒着我们,是何道理?”秋谷尚未开口,宝琴早已两颊通红,扭转身子,恰好与小松打个照面,更加不好意思,低下头去,口中咕噜道:“耐笃总是实梗瞎三话四,阿要无淘成,倪是要板面孔格。”秋谷听了好笑,便道:“这位方大少,天生的不老成,没有好话说的,你只当他放屁就是了。”又向小松道:“我向来作事从未瞒你,此处我实是今日第一回来,在余香阁点戏之后,钉梢回来的。你不信,只顾问房间里人便了。”那房间里娘姨阿彩、大姐阿仙,一齐说道:“方大少,勿要勿相信,轧实章大少是今朝做起格勒,倪阿肯骗耐嗄。”古小松听了,方才相信,想了一想,又摇摇头道:“我只不信。既然是今天做起,为甚你们先生的神气,倒像与章大少是老相好一样,是何道理?”小松说到此际,早被秋谷捏了一把,使个眼色,小松方才住口。秋谷悄悄埋怨他道:“你取笑也要看地方起的。我今天初次在此请客,你便如此胡言乱语,倘被他真个板起面孔来,你我岂不大家没趣?”小松笑道:“你不要来吓我,我是不怕的,你只好好的叫他转个局,我便不开口了,你肯不肯?”秋谷不觉大笑道:“原来你说了半天,是要割我的靴腰,何不早说,恰要绕着弯儿说呢?”便叫宝琴转过去坐在小松旁边。宝琴抬起头来,着实钉了秋谷一眼,也不言语。秋谷又催一遍,宝琴方才对着小松说道:“方大少,对勿住,倪间搭格规矩:一帮里客人勿做两个格。阿好谢谢耐,勿要扳倪格差头。倪情愿吃子一杯罚酒末哉。”说罢,便叫阿仙取出一只鸡缸杯来,斟了一杯热酒,立起身来,将杯照着小松,竟自吃干了。”小松倒也无可再言。停了一会,忽然笑道:“可恶可恶,我在堂子里头顽儿,总弄你这促掐鬼不过,你总要占个上风,究竟我同你是一样的人,难道我短了什么不成?”说着,又问宝琴道:“你看我们两人,倒底谁的风头好些?”宝琴听小松说得好笑,不免面红一笑,暗中又飞了秋谷一眼,早被对坐的客人名叫孔伯虚的看见,便笑道:“据我看来,秋翁与小翁二人正是工力愁敌,可算得瑜亮并生,一时无两。只是宝琴的意思有些看不上小翁,或是小翁的内才短些,比不上秋翁的精力,那我们外人就无从晓得了。”说得合席大笑起来。恰好各人的局陆续到了,彼此打断了话头。知酒过数巡,小松鼓起兴来,便要摆五十杯的庄。秋谷微笑道:“你这种的酒量也敢摆庄?待我来打坍你的。”于是攘臂而起,正与小松旗鼓相当。旁坐一个姓吴的劝道:“五十杯太多,留几杯等别人来打,你打了二十杯罢!”秋谷依了,便与小松五魁三元的叫了一阵。二十杯庄打完,秋谷自己也输了十五六杯,秋谷慢慢的喝了十杯,还有五杯,便折在一个大玻璃缸里,回过身来递与阿彩,叫他代饮。阿彩刚刚接过,早被宝琴劈手夺来,一口气咕嘟嘟的竟喝了一个干净,面上早红晕起来,放下杯子,那两只秋波水汪汪的更加了几分风韵。小松只顾与别人搳拳,竟不理会。秋谷却是留心的,见他杏眼微饧,桃腮带涩,心上觉得好生怜惜,只是说不出来,便低低的合他说道:“你何苦这样拼命的喝酒,喝醉了便怎样呢?”宝琴微笑不答,秋谷更是魂销。两人相视了好一会,小松的庄早已打完。小松除代酒外,自家也喝了三十余杯,觉得有些沉醉,从腰间掏出一个表来一看,早已指到十二点三刻了,便道:“时候不早了,我们散罢!好等你们两人细细的谈心。”上过干稀饭,各人都掏出两块洋钱放在桌上。秋谷也取出下脚四元,添菜两元,一齐放在台上。相帮进来收拾台面,把洋钱数了一数,七个客人共是十四块,一总二十块洋钱,便高叫一声:“多谢各位大少。”拿了洋钱出房去了。知看官且慢,你道此是什么规矩?原来姑苏书寓规条,大凡请客,须每位客人出台面洋两元,谓之”丢台面。”朋友请吃花酒,若非素日知己,不肯到场。因非但赔贴局钱,又要现丢台面,绝非上海请吃花酒,客人到了就算赏光的风俗。再加上海碰和一概二十元,苏州却无论长三幺二均是八元。以前上海青楼风俗,凡生客进门,倌人必唱京调或小曲一支,名为”堂唱”,恰须现钱开销。现在上海此例已除,姑苏却至今未改,这是苏、沪不同之处,在下预先一一申明,免得要受看官的指摘。主只说客人散后,只有秋谷未曾回去,就在那里借了一夜干铺。名说干铺,只怕明干暗湿也未可知,不在话下。古秋谷睡至晌午,方才起来,洗漱已毕,待要回栈,宝琴叫相帮到正元馆端了一碗一钱六分生炒鸡丝面来,让秋谷吃了;又亲自替秋谷梳了一条辫子,方才放他下楼,又叮嘱他晚上要来。秋谷一一答应了,自回栈去,仍就睡了。约至三下钟,方睡醒起来,随意吃些东西。正待出去,只见许宝琴家的阿仙笑嘻嘻的走进来,道:“章大少,阿是刚刚起来勒?倪先生到书场浪去哉,请耐去点戏。”秋谷也无可不可的,同了阿仙走到余香阁。主正待上楼,只见一顶倌人轿子停在门前,眼前觉得毫光一闪,走出一个倌人来,穿一件黑地银花外国缎灰鼠皮祆,下衬品蓝花缎裤子,玄色缎子弓鞋不到四寸,眉眼虽比许宝琴略逊,那一种的丰姿袅娜,骨格轻盈,却比许宝琴更加妩媚。秋谷立在扶梯边,一直等到他上了楼,目光尚有些定定的,被阿仙从后推了一把,道:“阿是看得头里向有点浑淘淘哉,快点上去哩!”秋谷被他一推,吓了一跳,不觉自己好笑,便走上扶梯,拣一个座位。刚刚坐下,堂倌早送了点戏牌过来,秋谷且不点戏,问着堂倌,那外国缎袄的叫甚名字。堂倌道:“他住在谈瀛里,名叫花云香,还是新近从上海来的,章老爷可要也点他两出?”秋谷要过笔来,便写了《二进宫》、《龙虎斗》、《探寒窑》、《铡美案》四出,都要花云香与许宝琴两人合唱。古堂倌喊了上去,花云香听得分明,回头一看,就是楼梯边的相遇人,不免低头一笑,随叫娘姨下来装烟。许宝琴却着实的钉了秋谷一眼。秋谷虽也看见,并不理会。花云香先了和弦,唱出一段《二进宫》,许宝琴随接唱下去,唱到末尾一句,两人一齐背过脸去,把琵琶放高一调,全用轮指合唱。那一声摇板却唱得顿挫抑扬,十分圆稳,秋谷喝一声采。随后又合唱了一出《铡美案》,许宝琴便先起身走了。只有花云香又独唱一出《探寒窑》,那喉咙愈唱愈高,愈高愈亮,唱到极高之后,一落千丈,就如银瓶落井一般,落到一半却又陡然提起,又如鹤唳入云,声声摇曳,真是珠喉遏月,逸响回风,只听得台下喝采之声轰然不绝。秋谷异常得意。花云香唱完之后,方才立起身来,正走秋谷面前经过,向秋谷点一点头,下楼去了。主秋谷见他走了,无精打采的付了帐,慢慢的下来。才到楼下,不防阿仙候在门口,便一把衣袖拉了秋谷,一直拉到甘棠桥,进门推他上楼。只见宝琴欲笑不笑,一付尴尬面孔,道:“章大少,耐倒有功夫到倪搭来坐坐,啥勿到花云香搭去嗄!”秋谷听了笑道:“你们这班人实在难说话得狠。叫了我来,又叫我到别处去,我就依着你的吩咐,到花家去。”说着,假做回身要走,早被阿仙一把拉住,说道:“耐阿要好意思格!花家里明朝去末哉,倪搭小场化,委屈耐点阿好?”宝琴接口说道:“耐放俚去嗫,看俚阿好意思走出去。”秋谷呵呵笑道:“你们不要我去,也就罢了,何必做出许多生意筋络来。”一面说,一面坐下。主宝琴问道:“阿要吃夜饭哉,就倪搭便饭,去叫仔两样菜阿好?”秋谷正待写菜去叫,只听楼下喊声“请客”。把请客条子递将上来一看,原来是小松请到如意里金黛玉家,上面写着:“容齐坐候入席”,秋谷便立起身来。阿仙便说道:“章大少,阿要带局去罢,省得来叫哉。”秋谷点头道:“也好。”因如意里与许家只隔一桥,便不用轿子,催许宝琴换好了出局衣裳,二人携手出门。知到了金黛玉家,问了房间,恰在楼下。小松早在房门口招呼,进房坐下,满房客人都与秋谷相识,不用套谈。小松见秋谷同着宝琴,便道:“你带局来,倒也简便,可还叫别人么?”秋谷因叫小松代写了一张花云香的局票,一同发去。主少时,大家入席,花云香早姗姗其来,进房含笑叫了一声,便坐在秋谷身后。秋谷不及应酬,便留心打量金黛玉的妆束,只见他:淡扫蛾眉,薄施脂粉,穿一件蜜色皮袄,衬一条妃色裤子。风鬟雾鬓,虽非倾国之姿;素口蛮腰,稳称芳菲之选。那边小松见了花云香,也打量了一会,忽嚷道:“不好了,又被你抢了一个去了!怎么我到处留心,总没有好的;你遇见的,总是好的呢?”秋谷道:“你为什么总是这样脾气?今天是你自己的主人,劝你少说两句罢!”说着,金黛玉起身斟了一巡酒,众客人的局也来了。花云香先唱了一出《取成都》,唱完了,对秋谷说声“献丑”,秋谷说声“辛苦”,便慢慢的谈起来。两人咬着耳朵不知讲些什么。许宝琴却看着冷笑。偶而秋谷回过身来同宝琴说话,宝琴却只是扭过身去,不肯理他。古秋谷正在没做理会处,小松斟了一大杯酒要与秋谷照杯,又笑道:“知己希逢,佳人难得,你快干了这一杯。”秋谷猛然听得,触起他的心事来,长叹一声,举杯一饮而尽,口中高吟道:“此时此景不沉醉,岂待三尺蓬蒿坟。”与小松彼此相对黯然。停了一回,小松方勉强笑道:“我们原是寻乐的,怎么倒寻起烦恼来呢?我与你还是喝酒罢。”秋谷也不回言,自己斟了一杯,又高吟道:“今日少年若长在。古之少年安在哉?”就又干了一杯。主花云香看见秋谷无故不乐,心中觉得十分难过,却又替他不得,便咬着秋谷耳朵道:“耐勿要煞死个吃酒哉,到倪搭去坐歇罢。耐坐仔我个轿子去阿好?”秋谷只点点头。花云香便叫自己的轿子来,亲手将秋谷扶在轿内,自己也立起身来,跟着走出,叫一部东洋车,傍着轿子同走。秋谷也不顾许宝琴,竟自到花家去了,连主人方小松都未招呼。正是:知名士风尘多涕泪,美人香草寄牢骚。古要知后事如何,且听下回分解。斋
第二回真抑塞粉墨登场假从良姑苏遇旧
只说方小松见秋谷不辞而别,也晓得他别有伤心,无不劝解,当下草草终席,小松便进城去了。秋谷自从坐着花云香的轿子,同到花家之后,便常在许、花二家走动,许宝琴虽只心中不悦,也无可如何。主开筵坐花,飞觞醉月,不觉已是一月有余。一日夜间,秋谷在花家吃过夜膳,想到二马路丹桂去看戏,便同着云香走出谈瀛里。那丹桂就在谈瀛里对门,不用轿子。走到戏园门口,案目认得秋谷,慌忙同了进去。苏州戏园没有厢楼,就在正桌坐下。主那时台上正在演那《翠屏山》,周凤林扮着潘巧云,虽然年纪大些,台容倒还不错。筱荣祥扮的杨雄,陈云仙扮的石秀,却也工力悉敌。末后陈云仙一路单刀,身眼手步,一丝不走,舞到妙处,就如一片电光,满身飞舞。秋谷见了高兴起来,忽然发一个奇想:自己想要粉墨登场,出一出胸中的郁勃之气。原来秋谷自幼投师习武,拳棒极精,等闲一二十人近他不得。打定主意,叫了案目过来,叫出开丹桂的老板郝尔铭走到座前。秋谷向来认得,便同他商议,要点一出《鸳鸯楼》,叫陈云仙扮武松,到那舞刀的一场,让秋谷自己登台试演,一场舞过,仍叫陈云仙上场。郝尔铭听了也觉诧异,踌躇一会,方才答应道:“照例是没有这个规矩,不过既是章老爷高兴,云仙又是我的徒弟,不比外来的武生,不妨迁就。”秋谷大喜,便取出两张十元的钞票交给他说:“这就算点戏的钱,我既硬出了这个新鲜主意,自然要多出些钱。”郝尔铭随意谢了一声收下,便走了进去,早见挂出一面点戏牌来。随后《翠屏山》唱完,便是《鸳鸯楼》出场,陈云仙仍扮武松,那脱靠的一场解数,筋斗跌扑,十分伶俐。此时秋谷早已走进戏房,打扮去了,花云香拦阻不住。古少时,陈云仙下去,只听得锣声一响,那板鼓的声音,打得犹如飘风疾雨一般,值场的掀开软帘,秋谷执刀在手,迅步登场。花云香见了,呆了一呆,觉得另换了一副英武的精神,绝非秋谷平时缓带轻裘的态度。只见他头紥玄缎包巾,上挽英雄结,身穿玄缎密扣紧身,四周用湖色缎镶嵌着灵芝如意,胸前白绒绳绕着双飞蝴蝶,腰紥月蓝带子约有四寸半阔,上钉着许多水钻,光华夺目,两边倒垂双扣,中间垂着湖色回须,下着黑绉纱兜裆叉裤,脚登玄缎挖嵌快靴,衬着这身装束,越显得狼腰猿臂,鹤势螂形。再加头上用一幅黑纱巾当头紧紥,紥得眼角眉梢高高吊起,那一派的英风锐气,直可辟易千人。加以秋谷出身贵介,天然台步从容,拳棒精通,自尔功夫圆稳。此时台上台下,眼睁睁的都看着秋谷一人。斋秋谷左手擎刀,用一个怀中抱月的架式,右手向上一横,亮开门户,霍地把身子一蹲,“拍”的一声,起了一个飞腿,收回右腿,缴转左腿,旋过身来,就势用个金鸡独立,右手接过刀来,慢慢的舞起。初时还松,后来渐紧,起初还见人影,后来只见刀光,那一把刀护着全身,丝毫不漏,只看见一团白光在台上滚来滚去,却没有一些脚步声音。说时迟,那时快,猛然见刀光一散,使一个燕子街泥,这一个筋斗,直从戏台东边直扑到台角,约有八九尺,那手中的刀便在自己脚下反折过来,“呼”的一声,收了刀法,现出全身,面上不红,心头不跳,仍用怀中抱月,收住了刀。正待进去,忽听得喝采声中,有一个妇女的声音十分清脆,高叫一声:“好呀!”主秋谷诧异起来,回头一看,只见二排上坐着一个二十岁上下的女子,衣装娇艳,态度妖娆,面目有些相熟,好像那里见过的一样,一双莹莹的眼波,只注在秋谷身上。照例武松舞刀一场,便要进去,此时秋谷见他看得认真,故意卖弄精神。好个章秋谷,另使出一番解数,把腰刀插在背后,空手开了一个四门,忽然左右开弓,连扑两交筋斗。翻过身来,脚跟尚未着地,那一把明晃晃的刀早掣在手中。这路刀法,与前更是不同,风声飒飒,冷气飕飕,刀光映着灯光,异常精采。这一路刀舞有半刻余钟,方才收住。进场换了衣服,下得台来,并不见一些儿杀气威风,依然是一个风流才子,台上仍换了陈云仙上场接演。主那知这一路刀,虽然不打紧,却引出一个人的故事来,就是那喝采的女子。你道是谁?就是三年前盛名之下的大金月兰。古这金月兰自从十七岁梳栊之后,不到一年,便有一个杭州黄大军机的长孙公子名叫黄伯润的,看中了他,花了八千银子的身价将他娶去,做了一位现现成成的姨太太。这位黄公子年方二十,正妻亡过,尚未续弦,性情极是温和,眉目也还清秀。家财巨万,门第清华。至于服食起居,更是一呼百诺,要一奉十。论起来,这金月兰也该自家知足,跟他过了一生,倘或生得一男半女,怕不是一位诰命夫人?岂非天外飞来的一段福分?主无奈上海这些做倌人的,骨相天生,万不能再做良家妇女。这班倌人,马夫、戏子是姘惯了,身体是散淡惯了,性情是放荡惯了,坐马车,游张园,吃大菜,看夜戏,天天如此,也觉得视为固然,行所无事。你叫他从良之后,怎生拘束得来?再如良家妇女,看得”失节”二字是一件极重大的事情;倌人出身的,只当作家常便饭一样,并不是什么奇事。就是那一班情愿从良的妓女,偶然见了一个俊俏后生,便由不得背地里私通款曲,这不过如家常便饭之外,偏背了一顿点心,算不是毁名败节,却轻轻的把一顶绿头巾暗暗送与主人公戴在头上。这还算是好的,更有那一种倌人,自己或是讨人,不能作主,或是欠了债项,不得自由,便拣一个有钱的客人,预先灌了无数迷汤,发下千斤重誓,一定要嫁那客人,身价不是三千,就是五千。这班寿头码子的客人却也奇怪:平时亲戚通融,友朋借贷,就立刻翻转面皮,倒反说穷告苦,非但一毛不拔,而且还要从此断绝往来;独到了遇着这种倌人,却情情愿愿,伏伏贴贴的,捧着大把的银子去孝敬他,还不敢说一个”不”字,好似儿子见了父母一样。这班人具着卑鄙龌龊的面目,怀着势利狭窄的心肠,那面目比纯钢炼就的还厚,那心肠比煤炭烧枯的还焦。目不识丁,偏会看不起读书种子;骨头鄙贱,偏要摆着那富贵的规模。真个是”投畀豺虎,豺虎不食;投畀有北,有北不受“的东西。他自己丧尽良心,所以就有丧尽良心的倌人来收拾他。归根花了一注大钱,不上一年半载,得个方便,卷了值钱的衣饰,远走高飞。那时非但人财两空,连他自家的血本都丢在东洋大海去了。这便叫“倌人淴浴”。借了他人的财力,自己拔出火坑;及至出了火坑,却又负义忘恩,全不顾人情天理。终究报应循环,丝毫不爽。自家拐骗的邪财,迟早原被那戏子、马夫一齐骗去。如此得来如此去,依旧是一双空手,蓄积毫无,到了年长色衰,门前冷落,这便追悔也追悔不来了。看官,你道上海的倌人可以娶得的么?古闲话少提,书归正传。只说金月兰嫁了黄公子之后,同到杭州,不上几时,便觉得十分拘束,渐渐的不惯起来,就撺掇黄公子,要赁房子住在上海。黄公子道:“你的意思无非拘束不惯,要去住在上海,好游园听戏,散散心情。但是上海地方不是可以长住得的,况且你更不比从前,做了良家妇女,就要诸事小心,就是住在上海,也不能时常出去。你既然嫁了我,便是我家的人,却要依着我家的规矩。别样事情我总可答应,这件事情是答应不来的,劝你不必起这念头罢。”主金月兰听了十分不悦,敢怒而不敢言,心中便有重落风尘之意。存了这条心念,便时时刻刻打算私逃。苦的是侯门如海,无计可施。好容易想着一个主意:那黄府的后进一带房屋,都是楼房,最后一进的后楼就靠着城河,城河内的船都停在黄府楼下,说话都听得见的。月兰便对公子说了,要搬到后楼去住,好看看往来船上的行人。黄公子梦里也想不到他要逃走,就应允了,任他搬去。月兰暗暗欢喜,拣了一个好日搬了上去。不多几时,买通了楼下一个船户,趁那夜黄公子不在房中,先把金银细软打了一个包袱,开了楼窗,在窗洞内吊将下去;然后自己也用一条汗巾,一头紧系窗搭,一头拴在自己腰间,又用两手紧紧扳住窗口,耐着惊吓,大着胆子,慢慢的在楼上坠下船来,连夜开船逃走,离了杭州,趁轮船到上海去了。古黄府直到明日午后,见月兰还不开门,方才疑惑。在门外大声叫唤,也不见有人答应。黄公子就晓得事情不妙,叫了两个家人打开了门,进去看时,那里有什么金月兰的影子?楼窗大开,箱笼抖乱。开箱看时,所有金珠首饰,值钱细软,都被他收拾一空。黄公子气得目瞪口呆,气了一会,也无可如何,只得取了月兰两张照片,并大略开了一个失单,已有万金开外,自己去拜钱塘县,托他上紧追拿,又请他发一角公文到上海缉访。一面写信知会华洋同知,将失单、照片一同寄去,叫包探认真探访。明知一时海阔天空,无从缉获,只好暂时放下,再作理会。因是为了此事,心中不乐,便也懒懒的坐在家中,有一月有余并未出去。屡次叫人到县里催过几趟,也并无影响。斋忽一日,钱塘县差了一个家人,来黄府报知公子,黄公子方才晓得金月兰现在上海,依旧挂牌应局。自从黄公子将照片、失单寄到上海之后,那华洋同知翁延寿便派了两个有名的包探,仔细采访。你想上海的包探何等精细,金月兰又不会改头换面,不多几日,早被两个包探访了出来,立时协同巡捕,将金月兰人赃并获,解到公堂。会审官略略问了几句,道:“我这里也不难为你,只把你移县解回杭州,等你主人自己发落就是了。”就把金月兰移交上海县收禁起来。上海县登时发了一角咨文到钱塘县,叫他派差来申,将金月兰提回核办。钱塘县接了咨文,连忙叫人到黄府送信,请示办法。斋黄公子听了,心中反又踌躇起来,暗想:月兰虽然可恶,既自己经逃走,便成覆水难收,若仍把他提到杭州追赃审问,岂不辱没了相府的门楣?况且耐着现在的凄凉,想到当初的恩爱,不觉心早软了一半。心中盘算了一回,打定主意,方对那差人道:“你回去上覆你们贵上。这金月兰虽是府中逃妾,但是张扬起来,未免声名不雅。据我看来,不必一定去办他逃走的罪名,只不许他再做生意,也就是了。请你们贵上就回一角文书,人也不必去提,只叫他具一个以后不再为娼的切结,再切实在上海县存一个案,如金月兰再在苏、杭、沪三处卖娼,便要彻底重究。你照我的话去说就是了。”钱塘差人诺诺连声,回去说了。钱塘县就发一角公文到上海县,存了一个案,准了金月兰具结取保出去,把一场天大的官司,化得来无影无踪,烟销火灭。知谁知金月兰江山好改,本性难移,只不敢在上海、苏、杭再做生意。闻得人说天津地方富盛,阔客极多,林黛玉、张书玉二人在天津不到两年,都是服用豪奢,外场阔绰,就是手中私蓄,何止万金,那衣饰尚不在数内,金月兰便想也到天津,投奔黛玉。他们本是要好姊妹,那有不收留他的道理。便收拾了随身的金珠衣服,趁了招商局新裕轮船的房舱。不一日,到了天津紫竹林。古停船上岸,好容易问到侯家后东天保南班林黛玉的寓所。黛玉见了月兰,惊喜交集,便问他如何脱身出来?月兰将逃走被拿、取保释放情形细说一遍,后说到上海不能再做生意,特地到天津投奔他的话。黛玉喜道:“这里正为人少做不出生意,要想去上海请人。我想近来上海的一班人也没有什么色艺双佳、擒纵客人的手段,所以我也不敢荐人。如今你既来此,甚是凑巧,那生意料想做得起的。我便叫本家替你预备房间,但房内的铺设是要的,两房间的陈设,少也要四五百块钱,你可打算得出么?”月兰道:“我身旁现银虽然不多,却有几十两金条在此,约莫也有二三千块钱,料想没有什么不够,这倒不用打算的。”黛玉更是欢喜,忙叫本家进来,说明缘故,要他预备房间。斋那女本家名叫阿毛,也是上海人,大姐出身,近来着实有些积蓄,所以到天津来开这爿南班堂子。此时听得金月兰要包他的房间,见月兰年纪尚轻,风头又好,也是高兴,便满口答应。月兰开了箱子,取出六十两金条来托他去换,正正换了三千多块钱。俗语:“有钱诸事办。”不上两日,把月兰的房间收拾得花团锦簇。当夜由黛玉的熟客,一个候补道姓钱的,替他摆了一个双台。主从此之后,果然车马盈门,和酒纷纷不绝。约有半年光景,开销之外多了二千开外的衣饰,三千余两的现银,月兰得意非常。古那晓得祸不单行,福无双至。恰值拳匪之乱,联军破了天津,林黛玉、金月兰等一齐狼狈南归。金月兰只逃得一个空身,那黄家卷出来的金珠也丢得干干净净。到了上海住不两日,联军又进了北京,信息一日紧似一日,风声鹤唳,草木皆兵。月兰是个惊弓之鸟,更加寝食不安,只得又逃到苏州暂时住下,再听消息,恰好与章秋谷同住佛照楼栈房。此时金月兰除了随身衣服、头上钗环之外,已是一无所有。主这一日偶然看戏,无心中遇着了秋谷。他从前在上海时,与秋谷虽然认识,一则记忆不真,二则也不知秋谷有这样的英雄本领,只觉得秋谷人才出众,气宇轩昂,那一把刀舞得来滚雪飞花,神出鬼没,不觉脱口而出,叫了一声:“好呀!”及至秋谷下台之后,走到月兰面前仔细一认,方才猛然记了起来,便对他笑道:“我瞧着就有点像你,只是有些模糊,原来到底是你。我们有二三年不见了,也不知那一阵风把你这红人儿吹到这苏州地面来了,只怕有什么事情罢?”原来秋谷虽是认得月兰,嫁与黄公子一节却并不晓得。斋金月兰此番到得苏州,两手空空,连房饭钱也无从设法,又不敢再做生意,正在进退两难、哭笑不得之际,见了秋谷,好似见了前世亲人一般,一把拉住道:“阿呀!果然是二少,我的事情一言难尽,好在我就住在此地佛照楼,你停回到我栈里去细细的说罢。”秋谷喜道:“我也是寓在佛照楼,凑巧得狠,等回儿回栈再说也好。”说着,仍到花云香桌上坐下。花云香早看得明白,冷笑道:“章大少,恭喜耐,咦到仔一位贵相知哉。”秋谷道:“你不要只管疑心。我从前在上海时就认得他的,并没有什么交情。你放心就是了。”云香道:“倪末阿有啥勿放心格,本来耐章大少格相好,阿关得倪啥事,倪是勿好来管耐格啘。”秋谷见他满面怒容,醋意可掬,便不去分说,只笑了一笑,只顾看戏。主台上《杀嫂》做完,换了小喜顺的《珍珠衫》上来。秋谷急欲同着金月兰回栈,要问问他的情形,却碍着花云香不便。恰巧云香的相帮走了进来,手中拿着几张局票来催云香去出党差,秋谷趁势叫他去罢,云香只得略坐一坐,立起来道:“难倪去哉,倪倒勿做啥讨厌人,等唔笃去随便那哼末哉。”秋谷也不理会,等到他去了,急急的走到月兰面前,低低说道:“这戏也没有什么看头,我们先回去罢!”月兰会意,点一点头,起身先走。随后秋谷出来,到了栈中,跟到金月兰房中坐下,二人方才剪烛长谈。斋月兰细细把数年事情一字不遗告诉了秋谷,说到那身世飘零之苦,不觉滴下泪来,秋谷也为之太息不止。正是:知襄王旧梦迷巫峡,子建新诗拟洛妃。古欲知后事,请听下回。斋
只说方小松见秋谷不辞而别,也晓得他别有伤心,无不劝解,当下草草终席,小松便进城去了。秋谷自从坐着花云香的轿子,同到花家之后,便常在许、花二家走动,许宝琴虽只心中不悦,也无可如何。主开筵坐花,飞觞醉月,不觉已是一月有余。一日夜间,秋谷在花家吃过夜膳,想到二马路丹桂去看戏,便同着云香走出谈瀛里。那丹桂就在谈瀛里对门,不用轿子。走到戏园门口,案目认得秋谷,慌忙同了进去。苏州戏园没有厢楼,就在正桌坐下。主那时台上正在演那《翠屏山》,周凤林扮着潘巧云,虽然年纪大些,台容倒还不错。筱荣祥扮的杨雄,陈云仙扮的石秀,却也工力悉敌。末后陈云仙一路单刀,身眼手步,一丝不走,舞到妙处,就如一片电光,满身飞舞。秋谷见了高兴起来,忽然发一个奇想:自己想要粉墨登场,出一出胸中的郁勃之气。原来秋谷自幼投师习武,拳棒极精,等闲一二十人近他不得。打定主意,叫了案目过来,叫出开丹桂的老板郝尔铭走到座前。秋谷向来认得,便同他商议,要点一出《鸳鸯楼》,叫陈云仙扮武松,到那舞刀的一场,让秋谷自己登台试演,一场舞过,仍叫陈云仙上场。郝尔铭听了也觉诧异,踌躇一会,方才答应道:“照例是没有这个规矩,不过既是章老爷高兴,云仙又是我的徒弟,不比外来的武生,不妨迁就。”秋谷大喜,便取出两张十元的钞票交给他说:“这就算点戏的钱,我既硬出了这个新鲜主意,自然要多出些钱。”郝尔铭随意谢了一声收下,便走了进去,早见挂出一面点戏牌来。随后《翠屏山》唱完,便是《鸳鸯楼》出场,陈云仙仍扮武松,那脱靠的一场解数,筋斗跌扑,十分伶俐。此时秋谷早已走进戏房,打扮去了,花云香拦阻不住。古少时,陈云仙下去,只听得锣声一响,那板鼓的声音,打得犹如飘风疾雨一般,值场的掀开软帘,秋谷执刀在手,迅步登场。花云香见了,呆了一呆,觉得另换了一副英武的精神,绝非秋谷平时缓带轻裘的态度。只见他头紥玄缎包巾,上挽英雄结,身穿玄缎密扣紧身,四周用湖色缎镶嵌着灵芝如意,胸前白绒绳绕着双飞蝴蝶,腰紥月蓝带子约有四寸半阔,上钉着许多水钻,光华夺目,两边倒垂双扣,中间垂着湖色回须,下着黑绉纱兜裆叉裤,脚登玄缎挖嵌快靴,衬着这身装束,越显得狼腰猿臂,鹤势螂形。再加头上用一幅黑纱巾当头紧紥,紥得眼角眉梢高高吊起,那一派的英风锐气,直可辟易千人。加以秋谷出身贵介,天然台步从容,拳棒精通,自尔功夫圆稳。此时台上台下,眼睁睁的都看着秋谷一人。斋秋谷左手擎刀,用一个怀中抱月的架式,右手向上一横,亮开门户,霍地把身子一蹲,“拍”的一声,起了一个飞腿,收回右腿,缴转左腿,旋过身来,就势用个金鸡独立,右手接过刀来,慢慢的舞起。初时还松,后来渐紧,起初还见人影,后来只见刀光,那一把刀护着全身,丝毫不漏,只看见一团白光在台上滚来滚去,却没有一些脚步声音。说时迟,那时快,猛然见刀光一散,使一个燕子街泥,这一个筋斗,直从戏台东边直扑到台角,约有八九尺,那手中的刀便在自己脚下反折过来,“呼”的一声,收了刀法,现出全身,面上不红,心头不跳,仍用怀中抱月,收住了刀。正待进去,忽听得喝采声中,有一个妇女的声音十分清脆,高叫一声:“好呀!”主秋谷诧异起来,回头一看,只见二排上坐着一个二十岁上下的女子,衣装娇艳,态度妖娆,面目有些相熟,好像那里见过的一样,一双莹莹的眼波,只注在秋谷身上。照例武松舞刀一场,便要进去,此时秋谷见他看得认真,故意卖弄精神。好个章秋谷,另使出一番解数,把腰刀插在背后,空手开了一个四门,忽然左右开弓,连扑两交筋斗。翻过身来,脚跟尚未着地,那一把明晃晃的刀早掣在手中。这路刀法,与前更是不同,风声飒飒,冷气飕飕,刀光映着灯光,异常精采。这一路刀舞有半刻余钟,方才收住。进场换了衣服,下得台来,并不见一些儿杀气威风,依然是一个风流才子,台上仍换了陈云仙上场接演。主那知这一路刀,虽然不打紧,却引出一个人的故事来,就是那喝采的女子。你道是谁?就是三年前盛名之下的大金月兰。古这金月兰自从十七岁梳栊之后,不到一年,便有一个杭州黄大军机的长孙公子名叫黄伯润的,看中了他,花了八千银子的身价将他娶去,做了一位现现成成的姨太太。这位黄公子年方二十,正妻亡过,尚未续弦,性情极是温和,眉目也还清秀。家财巨万,门第清华。至于服食起居,更是一呼百诺,要一奉十。论起来,这金月兰也该自家知足,跟他过了一生,倘或生得一男半女,怕不是一位诰命夫人?岂非天外飞来的一段福分?主无奈上海这些做倌人的,骨相天生,万不能再做良家妇女。这班倌人,马夫、戏子是姘惯了,身体是散淡惯了,性情是放荡惯了,坐马车,游张园,吃大菜,看夜戏,天天如此,也觉得视为固然,行所无事。你叫他从良之后,怎生拘束得来?再如良家妇女,看得”失节”二字是一件极重大的事情;倌人出身的,只当作家常便饭一样,并不是什么奇事。就是那一班情愿从良的妓女,偶然见了一个俊俏后生,便由不得背地里私通款曲,这不过如家常便饭之外,偏背了一顿点心,算不是毁名败节,却轻轻的把一顶绿头巾暗暗送与主人公戴在头上。这还算是好的,更有那一种倌人,自己或是讨人,不能作主,或是欠了债项,不得自由,便拣一个有钱的客人,预先灌了无数迷汤,发下千斤重誓,一定要嫁那客人,身价不是三千,就是五千。这班寿头码子的客人却也奇怪:平时亲戚通融,友朋借贷,就立刻翻转面皮,倒反说穷告苦,非但一毛不拔,而且还要从此断绝往来;独到了遇着这种倌人,却情情愿愿,伏伏贴贴的,捧着大把的银子去孝敬他,还不敢说一个”不”字,好似儿子见了父母一样。这班人具着卑鄙龌龊的面目,怀着势利狭窄的心肠,那面目比纯钢炼就的还厚,那心肠比煤炭烧枯的还焦。目不识丁,偏会看不起读书种子;骨头鄙贱,偏要摆着那富贵的规模。真个是”投畀豺虎,豺虎不食;投畀有北,有北不受“的东西。他自己丧尽良心,所以就有丧尽良心的倌人来收拾他。归根花了一注大钱,不上一年半载,得个方便,卷了值钱的衣饰,远走高飞。那时非但人财两空,连他自家的血本都丢在东洋大海去了。这便叫“倌人淴浴”。借了他人的财力,自己拔出火坑;及至出了火坑,却又负义忘恩,全不顾人情天理。终究报应循环,丝毫不爽。自家拐骗的邪财,迟早原被那戏子、马夫一齐骗去。如此得来如此去,依旧是一双空手,蓄积毫无,到了年长色衰,门前冷落,这便追悔也追悔不来了。看官,你道上海的倌人可以娶得的么?古闲话少提,书归正传。只说金月兰嫁了黄公子之后,同到杭州,不上几时,便觉得十分拘束,渐渐的不惯起来,就撺掇黄公子,要赁房子住在上海。黄公子道:“你的意思无非拘束不惯,要去住在上海,好游园听戏,散散心情。但是上海地方不是可以长住得的,况且你更不比从前,做了良家妇女,就要诸事小心,就是住在上海,也不能时常出去。你既然嫁了我,便是我家的人,却要依着我家的规矩。别样事情我总可答应,这件事情是答应不来的,劝你不必起这念头罢。”主金月兰听了十分不悦,敢怒而不敢言,心中便有重落风尘之意。存了这条心念,便时时刻刻打算私逃。苦的是侯门如海,无计可施。好容易想着一个主意:那黄府的后进一带房屋,都是楼房,最后一进的后楼就靠着城河,城河内的船都停在黄府楼下,说话都听得见的。月兰便对公子说了,要搬到后楼去住,好看看往来船上的行人。黄公子梦里也想不到他要逃走,就应允了,任他搬去。月兰暗暗欢喜,拣了一个好日搬了上去。不多几时,买通了楼下一个船户,趁那夜黄公子不在房中,先把金银细软打了一个包袱,开了楼窗,在窗洞内吊将下去;然后自己也用一条汗巾,一头紧系窗搭,一头拴在自己腰间,又用两手紧紧扳住窗口,耐着惊吓,大着胆子,慢慢的在楼上坠下船来,连夜开船逃走,离了杭州,趁轮船到上海去了。古黄府直到明日午后,见月兰还不开门,方才疑惑。在门外大声叫唤,也不见有人答应。黄公子就晓得事情不妙,叫了两个家人打开了门,进去看时,那里有什么金月兰的影子?楼窗大开,箱笼抖乱。开箱看时,所有金珠首饰,值钱细软,都被他收拾一空。黄公子气得目瞪口呆,气了一会,也无可如何,只得取了月兰两张照片,并大略开了一个失单,已有万金开外,自己去拜钱塘县,托他上紧追拿,又请他发一角公文到上海缉访。一面写信知会华洋同知,将失单、照片一同寄去,叫包探认真探访。明知一时海阔天空,无从缉获,只好暂时放下,再作理会。因是为了此事,心中不乐,便也懒懒的坐在家中,有一月有余并未出去。屡次叫人到县里催过几趟,也并无影响。斋忽一日,钱塘县差了一个家人,来黄府报知公子,黄公子方才晓得金月兰现在上海,依旧挂牌应局。自从黄公子将照片、失单寄到上海之后,那华洋同知翁延寿便派了两个有名的包探,仔细采访。你想上海的包探何等精细,金月兰又不会改头换面,不多几日,早被两个包探访了出来,立时协同巡捕,将金月兰人赃并获,解到公堂。会审官略略问了几句,道:“我这里也不难为你,只把你移县解回杭州,等你主人自己发落就是了。”就把金月兰移交上海县收禁起来。上海县登时发了一角咨文到钱塘县,叫他派差来申,将金月兰提回核办。钱塘县接了咨文,连忙叫人到黄府送信,请示办法。斋黄公子听了,心中反又踌躇起来,暗想:月兰虽然可恶,既自己经逃走,便成覆水难收,若仍把他提到杭州追赃审问,岂不辱没了相府的门楣?况且耐着现在的凄凉,想到当初的恩爱,不觉心早软了一半。心中盘算了一回,打定主意,方对那差人道:“你回去上覆你们贵上。这金月兰虽是府中逃妾,但是张扬起来,未免声名不雅。据我看来,不必一定去办他逃走的罪名,只不许他再做生意,也就是了。请你们贵上就回一角文书,人也不必去提,只叫他具一个以后不再为娼的切结,再切实在上海县存一个案,如金月兰再在苏、杭、沪三处卖娼,便要彻底重究。你照我的话去说就是了。”钱塘差人诺诺连声,回去说了。钱塘县就发一角公文到上海县,存了一个案,准了金月兰具结取保出去,把一场天大的官司,化得来无影无踪,烟销火灭。知谁知金月兰江山好改,本性难移,只不敢在上海、苏、杭再做生意。闻得人说天津地方富盛,阔客极多,林黛玉、张书玉二人在天津不到两年,都是服用豪奢,外场阔绰,就是手中私蓄,何止万金,那衣饰尚不在数内,金月兰便想也到天津,投奔黛玉。他们本是要好姊妹,那有不收留他的道理。便收拾了随身的金珠衣服,趁了招商局新裕轮船的房舱。不一日,到了天津紫竹林。古停船上岸,好容易问到侯家后东天保南班林黛玉的寓所。黛玉见了月兰,惊喜交集,便问他如何脱身出来?月兰将逃走被拿、取保释放情形细说一遍,后说到上海不能再做生意,特地到天津投奔他的话。黛玉喜道:“这里正为人少做不出生意,要想去上海请人。我想近来上海的一班人也没有什么色艺双佳、擒纵客人的手段,所以我也不敢荐人。如今你既来此,甚是凑巧,那生意料想做得起的。我便叫本家替你预备房间,但房内的铺设是要的,两房间的陈设,少也要四五百块钱,你可打算得出么?”月兰道:“我身旁现银虽然不多,却有几十两金条在此,约莫也有二三千块钱,料想没有什么不够,这倒不用打算的。”黛玉更是欢喜,忙叫本家进来,说明缘故,要他预备房间。斋那女本家名叫阿毛,也是上海人,大姐出身,近来着实有些积蓄,所以到天津来开这爿南班堂子。此时听得金月兰要包他的房间,见月兰年纪尚轻,风头又好,也是高兴,便满口答应。月兰开了箱子,取出六十两金条来托他去换,正正换了三千多块钱。俗语:“有钱诸事办。”不上两日,把月兰的房间收拾得花团锦簇。当夜由黛玉的熟客,一个候补道姓钱的,替他摆了一个双台。主从此之后,果然车马盈门,和酒纷纷不绝。约有半年光景,开销之外多了二千开外的衣饰,三千余两的现银,月兰得意非常。古那晓得祸不单行,福无双至。恰值拳匪之乱,联军破了天津,林黛玉、金月兰等一齐狼狈南归。金月兰只逃得一个空身,那黄家卷出来的金珠也丢得干干净净。到了上海住不两日,联军又进了北京,信息一日紧似一日,风声鹤唳,草木皆兵。月兰是个惊弓之鸟,更加寝食不安,只得又逃到苏州暂时住下,再听消息,恰好与章秋谷同住佛照楼栈房。此时金月兰除了随身衣服、头上钗环之外,已是一无所有。主这一日偶然看戏,无心中遇着了秋谷。他从前在上海时,与秋谷虽然认识,一则记忆不真,二则也不知秋谷有这样的英雄本领,只觉得秋谷人才出众,气宇轩昂,那一把刀舞得来滚雪飞花,神出鬼没,不觉脱口而出,叫了一声:“好呀!”及至秋谷下台之后,走到月兰面前仔细一认,方才猛然记了起来,便对他笑道:“我瞧着就有点像你,只是有些模糊,原来到底是你。我们有二三年不见了,也不知那一阵风把你这红人儿吹到这苏州地面来了,只怕有什么事情罢?”原来秋谷虽是认得月兰,嫁与黄公子一节却并不晓得。斋金月兰此番到得苏州,两手空空,连房饭钱也无从设法,又不敢再做生意,正在进退两难、哭笑不得之际,见了秋谷,好似见了前世亲人一般,一把拉住道:“阿呀!果然是二少,我的事情一言难尽,好在我就住在此地佛照楼,你停回到我栈里去细细的说罢。”秋谷喜道:“我也是寓在佛照楼,凑巧得狠,等回儿回栈再说也好。”说着,仍到花云香桌上坐下。花云香早看得明白,冷笑道:“章大少,恭喜耐,咦到仔一位贵相知哉。”秋谷道:“你不要只管疑心。我从前在上海时就认得他的,并没有什么交情。你放心就是了。”云香道:“倪末阿有啥勿放心格,本来耐章大少格相好,阿关得倪啥事,倪是勿好来管耐格啘。”秋谷见他满面怒容,醋意可掬,便不去分说,只笑了一笑,只顾看戏。主台上《杀嫂》做完,换了小喜顺的《珍珠衫》上来。秋谷急欲同着金月兰回栈,要问问他的情形,却碍着花云香不便。恰巧云香的相帮走了进来,手中拿着几张局票来催云香去出党差,秋谷趁势叫他去罢,云香只得略坐一坐,立起来道:“难倪去哉,倪倒勿做啥讨厌人,等唔笃去随便那哼末哉。”秋谷也不理会,等到他去了,急急的走到月兰面前,低低说道:“这戏也没有什么看头,我们先回去罢!”月兰会意,点一点头,起身先走。随后秋谷出来,到了栈中,跟到金月兰房中坐下,二人方才剪烛长谈。斋月兰细细把数年事情一字不遗告诉了秋谷,说到那身世飘零之苦,不觉滴下泪来,秋谷也为之太息不止。正是:知襄王旧梦迷巫峡,子建新诗拟洛妃。古欲知后事,请听下回。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