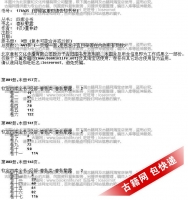楚庄王第一
"楚庄王杀陈夏征舒,《春秋》贬其文,不予专讨也;灵王杀齐庆封,而直称楚子,何也?"曰:"庄王之行贤,而征舒之罪重,以贤君讨重罪,其于人心善,若不贬,庸知其非正经,《春秋》常于其嫌得者,见其不得也。是故齐桓不予专地而封,晋文不予致王而朝,楚庄弗予专杀而讨,三者不得,则诸侯之得,殆此矣,此楚灵之所以称子而讨也。《春秋》之辞多所况,是文约而法明也。"问者曰:"不予诸侯之专封,复见于陈蔡之灭;不予诸侯之专讨,独不复见庆封之杀,何也?"曰:"《春秋》之用辞,已明者去之,未明者着之。今诸侯之不得专讨,固已明矣,而庆封之罪,未有所见也,故称楚子,以伯讨之,着其罪之宜死,以为天下大禁,曰:人臣之行,贬主之位,乱国之臣,虽不篡杀,其罪皆宜死。比于此,其云尔也。""《春秋》曰:'晋伐鲜虞。'奚恶乎晋,而同夷狄也?"曰:"春秋尊礼而重信,信重于地,礼尊于身。何以知其然也?宋伯姬疑礼而死于火,齐桓公疑信而亏其地,《春秋》贤而举之,以为天下法。曰礼而信,礼无不答,施无不报,天之数也。今我君臣同姓适女,女无良心,礼以不答,有恐畏我,何其不夷狄也!公子庆父之乱,鲁危殆亡,而齐桓安之,于彼无亲,尚来忧我,如何与同姓而残贼遇我。《诗》云:'宛彼鸣鸠,翰飞戾天。我心忧伤,念彼先人。明发不昧,有怀二人。'人皆有此心也。今晋不以同姓忧我,而强大厌我,我心望焉,故言之不好,谓之晋而已,婉辞也。"问者曰:"晋恶而不可亲,公往而不敢至,乃人情耳,君子何耻,而称公有疾也?"曰:"恶无故自来,君子不耻,内省不疚,何忧于志是已矣。今《春秋》耻之者,昭公有以取之也。臣陵其君,始于文而甚于昭,公受乱陵夷,而无惧惕之心,嚣嚣然轻计妄讨,犯大礼而取同姓,接不义而重自轻也。人之言曰:'国家治则四邻贺,国家乱则四邻散。'是故季孙专其位,而大国莫之正,出走八年,死乃得归,身亡子危,困之至也。君子不耻其困,而耻其所以穷。昭公虽逢此时,苟不取同姓,讵至于是;虽取同姓,能用孔子自辅,亦不至如是。时难而治简,行枉而无救,是其所以穷也。"
《春秋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:有见、有闻、有传闻。有见三世,有闻四世,有传闻五世。故哀、定、昭,君子之所见也,襄、成、文、宣,君子之所闻也,僖、闵、庄、桓、隐,君子之所传闻也。所见六十一年,所闻八十五年,所传闻九十六年。于所见,微其辞,于所闻,痛其祸,于传闻,杀其恩,与情俱也。是故逐季氏,而言又雩,微其辞也;子赤杀,弗忍书日,痛其祸也;子般杀,而书乙未,杀其恩也。屈伸之志,详略之文,皆应之,吾以其近近而远远、亲亲而疏疏也,亦知其贵贵而贱贱、重重而轻轻也,有知其厚厚而薄薄、善善而恶恶也,有知其阳阳而阴阴、白白而黑黑也。百物皆有合偶,偶之合之,仇之匹之,善矣。诗云:'威仪抑抑,德音秩秩,无怨无恶,率由仇匹。'此之谓也。然则《春秋》义之大者也,得一端而博达之,观其是非,可以得其正法,视其温辞,可以知其塞怨,是故于外道而不显,于内讳而不隐,于尊亦然,于贤亦然,此其别内外、差贤不肖、而等尊卑也。义不讪上,智不危身,故远者以义讳,近者以智畏,畏与义兼,则世逾近,而言逾谨矣,此定、哀之所以微其辞。以故用则天下平,不用则安其身,《春秋》之道也。
《春秋》之道,奉天而法古。是故虽有巧手,弗修规矩,不能正方圆;虽有察耳,不吹六律,不能定五音;虽有知心,不览先王,不能平天下;然则先王之遗道,亦天下之规矩六律已!故圣者法天,贤者法圣,此其大数也;得大数而治,失大数而乱,此治乱之分也;所闻天下无二道,故圣人异治同理也,古今通达,故先贤传其法于后世也。《春秋》之于世事也,善复古,讥易常,欲其法先王也。然而介以一言曰:"王者必改制。"自僻者得此以为辞,曰:"古苟可循,先王之道,何莫相因。"世迷是闻,以疑正道而信邪言,甚可患也。答之曰:"人有闻诸侯之君射狸首之乐者,于是自断狸首,县而射之,曰:'安在于乐也?'此闻其名,而不知其实者也。今所谓新王必改制者,非改其道,非变其理,受命于天,易姓更王,非继前王而王也,若一因前制,修故业,而无有所改,是与继前王而王者无以别。受命之君,天之所大显也;事父者承意,事君者仪志,事天亦然;今天大显已,物袭所代,而率与同,则不显不明,非天志,故必徒居处,更称号,改正朔,易服色者,无他焉,不敢不顺天志,而明自显也。若夫大纲,人伦道理,政治教化,习俗文义尽如故,亦何改哉!故王者有改制之名,无易道之实。孔子曰:'无为而治者,其舜乎!'言其王尧之道而已,此非不易之效与!"问者曰:"物改而天授,显矣,其必更作乐,何也?"曰:"乐异乎是,制为应天改之,乐为应人作之,彼之所受命者,必民之所同乐也。是故大改制于初,所以明天命也;更作乐于终,所以见天功也;缘天下之所新乐,而为之文,且以和政,且以兴德,天下未遍合和,王者不虚作乐,乐者,盈于内而动发于外者也,应其治时,制礼作乐以成之,成者本末质文,皆以具矣。是故作乐者,必反天下之所始乐于己以为本。舜时,民乐其昭尧之业也,故韶,韶者,昭也;禹之时,民乐其三圣相继,故夏,夏者,大也;汤之时,民乐其救之于患害也,故頀,頀者,救也;文王之时,民乐其兴师征伐也,故武,武者,伐也。四者天下同乐之,一也,其所同乐之端,不可一也。作乐之法,必反本之所乐,所乐不同事,乐安得不世异!是故舜作韶而禹作夏,汤作頀而文王作武,四乐殊名,则各顺其民始乐于己也,吾见其效矣。诗云:'文王受命,有此武功;既伐于崇,作邑于丰。'乐之风也。又曰:'王赫斯怒,爰整其旅。'当是时,纣为无道,诸侯大乱,民乐文王之怒,而歌咏之也。周人德已洽天下,反本以为乐,谓之大武,言民所始乐者,武也云尔。故凡乐者,作之于终,而名之以始,重本之义也。由此观之,正朔服色之改,受命应天,制礼作乐之异,人心之动也,二者离而复合,所为一也。"
玉杯第二
《春秋》讥文公以丧取。难者曰:"丧之法,不过三年,三年之丧,二十五月。今按经:文公乃四十一月方取,取时无丧,出其法也久矣,何以谓之丧取?"曰:"《春秋》之论事,莫重于志。今取必纳币,纳币之月在丧分,故谓之丧取也。且文公秋祫祭,以冬纳币,皆失于太蚤,《春秋》不讥其前,而顾讥其后,必以三年之丧,肌肤之情也,虽从俗而不能终,犹宜未平于心,今全无悼远之志,反思念取事,是《春秋》之所甚疾也,故讥不出三年,于首而已讥以丧取也,不别先后,贱其无人心也。缘此以论礼,礼之所重者,在其志,志敬而节具,则君子予之知礼;志和而音雅,则君子予之知乐;志哀而居约,则君子予之知丧。故曰非虚加之,重志之谓也。志为质,物为文,文着于质,质不居文,文安施质;质文两备,然后其礼成;文质偏行,不得有我尔之名;俱不能备,而偏行之,宁有质而无文,虽弗予能礼,尚少善之,介葛卢来是也;有文无质,非直不予,乃少恶之,谓州公寔来是也。然则《春秋》之序道也,先质而后文,右志而左物,故曰:'礼云礼云,玉帛云乎哉!'推而前之,亦宜曰:朝云朝云,辞令云乎哉!'乐云乐云,钟鼓云乎哉!'引而后之,亦宜曰:丧云丧云,衣服云乎哉!是故孔子立新王之道,明其贵志以反和,见其好诚以灭伪,其有继周之弊,故若此也。
《春秋》之法:以人随君,以君随天。曰:缘民臣之心,不可一日无君,一日不可无君,而犹三年称子者,为君心之未当立也,此非以人随君耶!孝子之心,三年不当,而逾年即位者,与天数俱终始也,此非以君随天邪!故屈民而伸君,屈君而伸天,《春秋》之大义也。
《春秋》论十二世之事,人道浃而王道备,法布二百四十二年之中,相为左右,以成文采,其居参错,非袭古也。是故论《春秋》者,合而通之,缘而求之,五其比,偶其类,览其绪,屠其赘,是以人道浃而王法立。以为不然,今夫天子逾年即位,诸侯于封内三年称子,皆不在经也,而操之与在经无以异,非无其辨也,有所见而经安受其赘也,故能以比贯类,以辨付赘者,大得之矣。
人受命于天,有善善恶恶之性,可养而不可改,可豫而不可去,若形体之可肥轹而不可得革也。是故虽有至贤,能为君亲含容其恶,不能为君亲令无恶。书曰:"厥辟去厥只"事亲亦然,皆忠孝之极也,非至贤安能如是。父不父则子不子,君不君则臣不臣耳。
文公不能服丧,不时奉祭,不以三年,又以丧取,取于大夫,以卑宗庙,乱其群祖,以逆先公,小善无一,而大恶四五;故诸侯弗予盟,命大夫弗为使,是恶恶之征,不臣之效也。出侮于外,入夺于内,无位之君也。孔子曰:"政逮于大夫,四世矣。"盖自文公以来之谓也。
君子知在位者不能以恶服人也,是故简六艺以赡养之。诗书序其志,礼乐纯其美,《易》、《春秋》明其知,六学皆大,而各有所长。诗道志,故长于质;礼制节,故长于文;乐咏德,故长于风;书着功,故长于事;易本天地,故长于数;春秋正是非,故长于治人;能兼得其所长,而不能遍举其详也。故人主大节则知闇,大博则业厌,二者异失同贬,其伤必至,不可不察也。是故善为师者,既美其道,有慎其行,齐时蚤晚,任多少,适疾徐,造而勿趋,稽而勿苦,省其所为,而成其所湛,故力不劳,而身大成,此之谓圣化,吾取之。
《春秋》之好微与,其贵志也。春秋修本末之义,达变故之应,通生死之志,遂人道之极者也。是故君杀贼讨,则善而书其诛;若莫之讨,则君不书葬,而贼不复见矣。不书葬,以为无臣子也;贼不复见,以其宜灭绝也。今赵盾弑君,四年之后,别牍复见,非《春秋》之常辞也。古今之学者异而问之曰:"是弑君,何以复见?犹曰贼未讨,何以书葬?何以书葬者,不宜书葬也而书葬;何以复见者,亦不宜复见也而复见;二者同贯,不得不相若也。盾之复见,直以赴问而辨不亲弑,非不当诛也;则亦不得不谓悼公之书葬,直以赴问而辨不成弑,非不当罪也。若是则《春秋》之说乱矣,岂可法哉!""故贯比而论,是非虽难悉得,其义一也。今盾诛无传,弗诛无传,以比言之,法论也,无比而处之,诬辞也,今视其比,皆不当死,何以诛之。《春秋》赴问数百,应问数千,同留经中,翻援比类,以发其端,卒无妄言,而得应于传者;今使外贼不可诛,故皆复见,而问曰:'此复见,何也?'言莫妄于是,何以得应乎!故吾以其得应,知其问之不妄,以其问之不妄,知盾之狱不可不察也。夫名为弑父,而实免罪者,已有之矣;亦有名为弑君,而罪不诛者,逆而距之,不若徐而味之,且吾语盾有本,诗云:'他人有心,予忖度之。'此言物莫无邻,察视其外,可以见其内也。今案盾事,而观其心,愿而不刑,合而信之,非篡弑之邻也,按盾辞号乎天,苟内不诚,安能如是,是故训其终始,无弑之志,枸恶谋者,过在不遂去,罪在不讨贼而已。臣之宜为君讨贼也,犹子之宜为父尝药也;子不尝药,故加之弑父,臣不讨贼,故加之弑君,其义一也。所以示天下废臣子之节,其恶之大若此也。故盾之不讨贼为弑君也,与止之不尝药为弑父无以异,盾不宜诛,以此参之。"问者曰:"夫谓之弑,而有不诛,其论难知,非蒙之所能见也。故赦止之罪,以传明之;盾不诛,无传,何也?"曰:"世乱义废,背上不臣,篡弑覆君者多,而有明大恶之诛,谁言其诛?故晋赵盾、楚公子比皆不诛之文,而弗为传,弗欲明之心也。"问者曰:"人弑其君,重卿在而弗能讨者,非一国也。灵公弑,赵盾不在,不在之与在,恶有厚薄,《春秋》责在而不讨贼者,弗系臣子尔也;责不在而不讨贼者,乃加弑焉,何其责厚恶之薄,薄恶之厚也?"曰:"《春秋》之道,视人所惑,为立说以大明之。今赵盾贤,而不遂于理,皆见其善,莫见其罪,故因其所贤,而加之大恶,系之重责,使人湛思,而自省悟以反道,曰:'吁!君臣之大义,父子之道,乃至乎此。'此所由恶薄而责之厚也;他国不讨贼者,诸斗筲之民,何足数哉!弗系人数而已,此所由恶厚而责薄也。传曰:'轻为重,重为轻。'非是之谓乎!故公子比嫌可以立,赵盾嫌无臣责,许止嫌无子罪,《春秋》为人不知恶,而恬行不备也,是故重累责之,以缫枉世而直之,缫者不过其正弗能直,知此而义毕矣。"
《春秋繁露》 汉·董仲舒
"楚庄王杀陈夏征舒,《春秋》贬其文,不予专讨也;灵王杀齐庆封,而直称楚子,何也?"曰:"庄王之行贤,而征舒之罪重,以贤君讨重罪,其于人心善,若不贬,庸知其非正经,《春秋》常于其嫌得者,见其不得也。是故齐桓不予专地而封,晋文不予致王而朝,楚庄弗予专杀而讨,三者不得,则诸侯之得,殆此矣,此楚灵之所以称子而讨也。《春秋》之辞多所况,是文约而法明也。"问者曰:"不予诸侯之专封,复见于陈蔡之灭;不予诸侯之专讨,独不复见庆封之杀,何也?"曰:"《春秋》之用辞,已明者去之,未明者着之。今诸侯之不得专讨,固已明矣,而庆封之罪,未有所见也,故称楚子,以伯讨之,着其罪之宜死,以为天下大禁,曰:人臣之行,贬主之位,乱国之臣,虽不篡杀,其罪皆宜死。比于此,其云尔也。""《春秋》曰:'晋伐鲜虞。'奚恶乎晋,而同夷狄也?"曰:"春秋尊礼而重信,信重于地,礼尊于身。何以知其然也?宋伯姬疑礼而死于火,齐桓公疑信而亏其地,《春秋》贤而举之,以为天下法。曰礼而信,礼无不答,施无不报,天之数也。今我君臣同姓适女,女无良心,礼以不答,有恐畏我,何其不夷狄也!公子庆父之乱,鲁危殆亡,而齐桓安之,于彼无亲,尚来忧我,如何与同姓而残贼遇我。《诗》云:'宛彼鸣鸠,翰飞戾天。我心忧伤,念彼先人。明发不昧,有怀二人。'人皆有此心也。今晋不以同姓忧我,而强大厌我,我心望焉,故言之不好,谓之晋而已,婉辞也。"问者曰:"晋恶而不可亲,公往而不敢至,乃人情耳,君子何耻,而称公有疾也?"曰:"恶无故自来,君子不耻,内省不疚,何忧于志是已矣。今《春秋》耻之者,昭公有以取之也。臣陵其君,始于文而甚于昭,公受乱陵夷,而无惧惕之心,嚣嚣然轻计妄讨,犯大礼而取同姓,接不义而重自轻也。人之言曰:'国家治则四邻贺,国家乱则四邻散。'是故季孙专其位,而大国莫之正,出走八年,死乃得归,身亡子危,困之至也。君子不耻其困,而耻其所以穷。昭公虽逢此时,苟不取同姓,讵至于是;虽取同姓,能用孔子自辅,亦不至如是。时难而治简,行枉而无救,是其所以穷也。"
《春秋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:有见、有闻、有传闻。有见三世,有闻四世,有传闻五世。故哀、定、昭,君子之所见也,襄、成、文、宣,君子之所闻也,僖、闵、庄、桓、隐,君子之所传闻也。所见六十一年,所闻八十五年,所传闻九十六年。于所见,微其辞,于所闻,痛其祸,于传闻,杀其恩,与情俱也。是故逐季氏,而言又雩,微其辞也;子赤杀,弗忍书日,痛其祸也;子般杀,而书乙未,杀其恩也。屈伸之志,详略之文,皆应之,吾以其近近而远远、亲亲而疏疏也,亦知其贵贵而贱贱、重重而轻轻也,有知其厚厚而薄薄、善善而恶恶也,有知其阳阳而阴阴、白白而黑黑也。百物皆有合偶,偶之合之,仇之匹之,善矣。诗云:'威仪抑抑,德音秩秩,无怨无恶,率由仇匹。'此之谓也。然则《春秋》义之大者也,得一端而博达之,观其是非,可以得其正法,视其温辞,可以知其塞怨,是故于外道而不显,于内讳而不隐,于尊亦然,于贤亦然,此其别内外、差贤不肖、而等尊卑也。义不讪上,智不危身,故远者以义讳,近者以智畏,畏与义兼,则世逾近,而言逾谨矣,此定、哀之所以微其辞。以故用则天下平,不用则安其身,《春秋》之道也。
《春秋》之道,奉天而法古。是故虽有巧手,弗修规矩,不能正方圆;虽有察耳,不吹六律,不能定五音;虽有知心,不览先王,不能平天下;然则先王之遗道,亦天下之规矩六律已!故圣者法天,贤者法圣,此其大数也;得大数而治,失大数而乱,此治乱之分也;所闻天下无二道,故圣人异治同理也,古今通达,故先贤传其法于后世也。《春秋》之于世事也,善复古,讥易常,欲其法先王也。然而介以一言曰:"王者必改制。"自僻者得此以为辞,曰:"古苟可循,先王之道,何莫相因。"世迷是闻,以疑正道而信邪言,甚可患也。答之曰:"人有闻诸侯之君射狸首之乐者,于是自断狸首,县而射之,曰:'安在于乐也?'此闻其名,而不知其实者也。今所谓新王必改制者,非改其道,非变其理,受命于天,易姓更王,非继前王而王也,若一因前制,修故业,而无有所改,是与继前王而王者无以别。受命之君,天之所大显也;事父者承意,事君者仪志,事天亦然;今天大显已,物袭所代,而率与同,则不显不明,非天志,故必徒居处,更称号,改正朔,易服色者,无他焉,不敢不顺天志,而明自显也。若夫大纲,人伦道理,政治教化,习俗文义尽如故,亦何改哉!故王者有改制之名,无易道之实。孔子曰:'无为而治者,其舜乎!'言其王尧之道而已,此非不易之效与!"问者曰:"物改而天授,显矣,其必更作乐,何也?"曰:"乐异乎是,制为应天改之,乐为应人作之,彼之所受命者,必民之所同乐也。是故大改制于初,所以明天命也;更作乐于终,所以见天功也;缘天下之所新乐,而为之文,且以和政,且以兴德,天下未遍合和,王者不虚作乐,乐者,盈于内而动发于外者也,应其治时,制礼作乐以成之,成者本末质文,皆以具矣。是故作乐者,必反天下之所始乐于己以为本。舜时,民乐其昭尧之业也,故韶,韶者,昭也;禹之时,民乐其三圣相继,故夏,夏者,大也;汤之时,民乐其救之于患害也,故頀,頀者,救也;文王之时,民乐其兴师征伐也,故武,武者,伐也。四者天下同乐之,一也,其所同乐之端,不可一也。作乐之法,必反本之所乐,所乐不同事,乐安得不世异!是故舜作韶而禹作夏,汤作頀而文王作武,四乐殊名,则各顺其民始乐于己也,吾见其效矣。诗云:'文王受命,有此武功;既伐于崇,作邑于丰。'乐之风也。又曰:'王赫斯怒,爰整其旅。'当是时,纣为无道,诸侯大乱,民乐文王之怒,而歌咏之也。周人德已洽天下,反本以为乐,谓之大武,言民所始乐者,武也云尔。故凡乐者,作之于终,而名之以始,重本之义也。由此观之,正朔服色之改,受命应天,制礼作乐之异,人心之动也,二者离而复合,所为一也。"
玉杯第二
《春秋》讥文公以丧取。难者曰:"丧之法,不过三年,三年之丧,二十五月。今按经:文公乃四十一月方取,取时无丧,出其法也久矣,何以谓之丧取?"曰:"《春秋》之论事,莫重于志。今取必纳币,纳币之月在丧分,故谓之丧取也。且文公秋祫祭,以冬纳币,皆失于太蚤,《春秋》不讥其前,而顾讥其后,必以三年之丧,肌肤之情也,虽从俗而不能终,犹宜未平于心,今全无悼远之志,反思念取事,是《春秋》之所甚疾也,故讥不出三年,于首而已讥以丧取也,不别先后,贱其无人心也。缘此以论礼,礼之所重者,在其志,志敬而节具,则君子予之知礼;志和而音雅,则君子予之知乐;志哀而居约,则君子予之知丧。故曰非虚加之,重志之谓也。志为质,物为文,文着于质,质不居文,文安施质;质文两备,然后其礼成;文质偏行,不得有我尔之名;俱不能备,而偏行之,宁有质而无文,虽弗予能礼,尚少善之,介葛卢来是也;有文无质,非直不予,乃少恶之,谓州公寔来是也。然则《春秋》之序道也,先质而后文,右志而左物,故曰:'礼云礼云,玉帛云乎哉!'推而前之,亦宜曰:朝云朝云,辞令云乎哉!'乐云乐云,钟鼓云乎哉!'引而后之,亦宜曰:丧云丧云,衣服云乎哉!是故孔子立新王之道,明其贵志以反和,见其好诚以灭伪,其有继周之弊,故若此也。
《春秋》之法:以人随君,以君随天。曰:缘民臣之心,不可一日无君,一日不可无君,而犹三年称子者,为君心之未当立也,此非以人随君耶!孝子之心,三年不当,而逾年即位者,与天数俱终始也,此非以君随天邪!故屈民而伸君,屈君而伸天,《春秋》之大义也。
《春秋》论十二世之事,人道浃而王道备,法布二百四十二年之中,相为左右,以成文采,其居参错,非袭古也。是故论《春秋》者,合而通之,缘而求之,五其比,偶其类,览其绪,屠其赘,是以人道浃而王法立。以为不然,今夫天子逾年即位,诸侯于封内三年称子,皆不在经也,而操之与在经无以异,非无其辨也,有所见而经安受其赘也,故能以比贯类,以辨付赘者,大得之矣。
人受命于天,有善善恶恶之性,可养而不可改,可豫而不可去,若形体之可肥轹而不可得革也。是故虽有至贤,能为君亲含容其恶,不能为君亲令无恶。书曰:"厥辟去厥只"事亲亦然,皆忠孝之极也,非至贤安能如是。父不父则子不子,君不君则臣不臣耳。
文公不能服丧,不时奉祭,不以三年,又以丧取,取于大夫,以卑宗庙,乱其群祖,以逆先公,小善无一,而大恶四五;故诸侯弗予盟,命大夫弗为使,是恶恶之征,不臣之效也。出侮于外,入夺于内,无位之君也。孔子曰:"政逮于大夫,四世矣。"盖自文公以来之谓也。
君子知在位者不能以恶服人也,是故简六艺以赡养之。诗书序其志,礼乐纯其美,《易》、《春秋》明其知,六学皆大,而各有所长。诗道志,故长于质;礼制节,故长于文;乐咏德,故长于风;书着功,故长于事;易本天地,故长于数;春秋正是非,故长于治人;能兼得其所长,而不能遍举其详也。故人主大节则知闇,大博则业厌,二者异失同贬,其伤必至,不可不察也。是故善为师者,既美其道,有慎其行,齐时蚤晚,任多少,适疾徐,造而勿趋,稽而勿苦,省其所为,而成其所湛,故力不劳,而身大成,此之谓圣化,吾取之。
《春秋》之好微与,其贵志也。春秋修本末之义,达变故之应,通生死之志,遂人道之极者也。是故君杀贼讨,则善而书其诛;若莫之讨,则君不书葬,而贼不复见矣。不书葬,以为无臣子也;贼不复见,以其宜灭绝也。今赵盾弑君,四年之后,别牍复见,非《春秋》之常辞也。古今之学者异而问之曰:"是弑君,何以复见?犹曰贼未讨,何以书葬?何以书葬者,不宜书葬也而书葬;何以复见者,亦不宜复见也而复见;二者同贯,不得不相若也。盾之复见,直以赴问而辨不亲弑,非不当诛也;则亦不得不谓悼公之书葬,直以赴问而辨不成弑,非不当罪也。若是则《春秋》之说乱矣,岂可法哉!""故贯比而论,是非虽难悉得,其义一也。今盾诛无传,弗诛无传,以比言之,法论也,无比而处之,诬辞也,今视其比,皆不当死,何以诛之。《春秋》赴问数百,应问数千,同留经中,翻援比类,以发其端,卒无妄言,而得应于传者;今使外贼不可诛,故皆复见,而问曰:'此复见,何也?'言莫妄于是,何以得应乎!故吾以其得应,知其问之不妄,以其问之不妄,知盾之狱不可不察也。夫名为弑父,而实免罪者,已有之矣;亦有名为弑君,而罪不诛者,逆而距之,不若徐而味之,且吾语盾有本,诗云:'他人有心,予忖度之。'此言物莫无邻,察视其外,可以见其内也。今案盾事,而观其心,愿而不刑,合而信之,非篡弑之邻也,按盾辞号乎天,苟内不诚,安能如是,是故训其终始,无弑之志,枸恶谋者,过在不遂去,罪在不讨贼而已。臣之宜为君讨贼也,犹子之宜为父尝药也;子不尝药,故加之弑父,臣不讨贼,故加之弑君,其义一也。所以示天下废臣子之节,其恶之大若此也。故盾之不讨贼为弑君也,与止之不尝药为弑父无以异,盾不宜诛,以此参之。"问者曰:"夫谓之弑,而有不诛,其论难知,非蒙之所能见也。故赦止之罪,以传明之;盾不诛,无传,何也?"曰:"世乱义废,背上不臣,篡弑覆君者多,而有明大恶之诛,谁言其诛?故晋赵盾、楚公子比皆不诛之文,而弗为传,弗欲明之心也。"问者曰:"人弑其君,重卿在而弗能讨者,非一国也。灵公弑,赵盾不在,不在之与在,恶有厚薄,《春秋》责在而不讨贼者,弗系臣子尔也;责不在而不讨贼者,乃加弑焉,何其责厚恶之薄,薄恶之厚也?"曰:"《春秋》之道,视人所惑,为立说以大明之。今赵盾贤,而不遂于理,皆见其善,莫见其罪,故因其所贤,而加之大恶,系之重责,使人湛思,而自省悟以反道,曰:'吁!君臣之大义,父子之道,乃至乎此。'此所由恶薄而责之厚也;他国不讨贼者,诸斗筲之民,何足数哉!弗系人数而已,此所由恶厚而责薄也。传曰:'轻为重,重为轻。'非是之谓乎!故公子比嫌可以立,赵盾嫌无臣责,许止嫌无子罪,《春秋》为人不知恶,而恬行不备也,是故重累责之,以缫枉世而直之,缫者不过其正弗能直,知此而义毕矣。"
《春秋繁露》 汉·董仲舒
竹林第三
《春秋》之常辞也,不予夷狄,而予中国为礼,至邲之战,偏然反之,何也?"曰:"《春秋》无通辞,从变而移,今晋变而为夷狄,楚变而为君子,故移其辞以从其事。夫庄王之舍郑,有可贵之美,晋人不知其善,而欲击之,所救已解,如挑与之战,此无善善之心,而轻救民之意也,是以贱之,而不使得与贤者为礼。秦穆侮蹇叔而大败,郑文轻众而丧师,《春秋》之敬贤重民如是。是故战攻侵伐,虽数百起,必一二书,伤其害所重也。"问者曰:"其书战伐甚谨,其恶战伐无辞,何也?"曰:"会同之事,大者主小,战伐之事,后者主先,苟不恶,何为使起之者居下,是其恶战伐之辞已!且《春秋》之法,凶年不修旧,意在无苦民尔;苦民尚恶之,况伤民乎!伤民尚痛之,况杀民乎!故曰:凶年修旧则讥,造邑则讳,是害民之小者,恶之小也;害民之大者,恶之大也,今战伐之于民,其为害几何!考意而观指,则《春秋》之所恶者,不任德而任力,驱民而残贼之;其所好者,设而勿用,仁义以服之也。《诗》云:'弛其文德,洽此四国。'此《春秋》之所善也。夫德不足以亲近,而文不足以来远,而断断以战伐为之者,此固《春秋》所甚疾已,皆非义也。"难者曰:"春秋之书战伐也,有恶有善也,恶轴击而善偏战,耻伐丧而荣复雠,奈何以《春秋》为无义战而尽恶之也?"曰:"凡春秋之记灾异也,虽亩有数茎,犹谓之无麦苗也;今天下之大,三百年之久,战攻侵伐,不可胜数,而复雠者有二焉,是何以异于无麦苗之有数茎哉!不足以难之,故谓之无义战也。以无义战为不可,则无麦苗亦不可也;以无麦苗为可,则无义战亦可矣。若《春秋》之于偏战也,善其偏,不善其战,有以效其然也。春秋爱人,而战者杀人,君子奚说善杀其所爱哉!故《春秋》之于偏战也,犹其于诸夏也,引之鲁,则谓之外,引之夷狄,则谓之内;比之轴战,则谓之义,比之不战,则谓之不义;故盟不如不盟,然而有所谓善盟;战不如不战,然而有所谓善战;不义之中有义,义之中有不义;辞不能及,皆在于指,非精心达思者,其庸能知之!诗云:'棠棣之华,偏其反而;岂不尔思,室是远而。'孔子曰:'未之思也!夫何远之有?'由是观之,见其指者,不任其辞,不任其辞,然后可与适道矣。"
"司马子反为君使,废君命,与敌情,从其所请,与宋平,是内专政,而外擅名也。专政则轻君,擅名则不臣,而春秋大之,奚由哉?"曰:"为其有惨怛之恩,不忍饿一国之民,使之相食。推恩者远之为大,为仁者自然为美。今子反出己之心,矜宋之民,无计其闲,故大之也。"难者曰:"《春秋》之法,卿不忧诸侯,政不在大夫。子反为楚臣,而恤宋民,是忧诸侯也;不复其君,而与敌平,是政在大夫也。湨梁之盟,信在大夫,而春秋刺之,为其夺君尊也;平在大夫,亦夺君尊,而《春秋》大之,此所闲也。且《春秋》之义,臣有恶擅名美。故忠臣不显谏,欲其由君出也。《书》曰:'尔有嘉谋嘉猷,入告尔君于内,尔乃顺之于外,曰:此谋此猷,惟我君之德。'此为人臣之法也;古之良大夫,其事君皆若是。今子反去君近而不复,庄王可见而不告,皆以其解二国之难,为不得已也,奈其夺君名美何!此所惑也。"曰:"《春秋》之道,固有常有变,变用于变,常用于常,各止其科,非相妨也。今诸子所称,皆天下之常,雷同之义也;子反之行,一曲之变,独修之意也。夫目惊而体失其容,心惊而事有所忘,人之情也;通于惊之情者,取其一美,不尽其失。诗云:'采葑采菲,无以下体。'此之谓也。今子反往视宋,闻人相食,大惊而哀之,不意之至于此也,是以心骇目动,而违常礼。礼者,庶于仁,文质而成体者也。今使人相食,大失其仁,安着其礼,方救其质,奚恤其文,故曰:'当仁不让。'此之谓也。《春秋》之辞,有所谓贱者,有贱乎贱者,夫有贱乎贱者,则亦有贵乎贵者矣。今让者,《春秋》之所贵,虽然,见人相食,惊人相爨,救之忘其让,君子之道,有贵于让者也,故说春秋者,无以平定之常义,疑变故之大,则义几可谕矣。"
《春秋》记天下之得失,而见所以然之故,甚幽而明,无传而着,不可不察也。夫泰山之为大,弗察弗见,而况微眇者乎!故按春秋而适往事,穷其端而视其故,得志之君子、有喜之人,不可不慎也。齐顷公亲齐桓公之孙,国固广大,而地势便利矣,又得霸主之余尊,而志加于诸侯,以此之故,难使会同,而易使骄奢,即位九年,末尝肯一与会同之事,有怒鲁卫之志,而不从诸侯于清丘断道,春往伐鲁,入其北郊,顾返伐卫,败之新筑;当是时也,方乘胜而志广,大国往聘,慢而弗敬其使者,晋鲁俱怒,内悉其众,外得党与卫曹,四国相辅,大困之鞍,获齐顷公,斮逄丑父。深本顷公之所以大辱身,几亡国,为天下笑,其端乃从慑鲁胜卫起;伐鲁,鲁不敢出;击卫,大败之;因得气而无敌国,以兴患也。故曰:得志有喜,不可不戒。此其效也。自是之后,顷公恐惧,不听声乐,不饮酒食肉,内爱百姓,问疾吊丧,外敬诸侯,从会与盟,卒终其身,家国安宁。是福之本生于忧,而祸起于喜也。呜呼!物之所由然,其于人切近,可不省邪!
"逄丑父杀其身以生其君,何以不得谓知权?丑父欺晋,祭仲许宋,俱枉正以存其君,然而丑父之所为,难于祭仲,祭仲见贤,而丑父犹见非,何也?"曰:"是非难别者在此,此其嫌疑相似,而不同理者,不可不察。夫去位而避兄弟者,君子之所甚贵;获虏逃遁者,君子之所甚贱。祭仲措其君于人所甚贵,以生其君,故春秋以为知权而贤之;丑父措其君于人所甚贱,以生其君,春秋以为不知权而简之。其俱枉正以存君,相似也,其使君荣之,与使君辱,不同理。故凡人之有为也,前枉而后义者,谓之中权,虽不能成,春秋善之,鲁隐公、郑祭仲是也;前正而后有枉者,谓之邪道,虽能成之,春秋不爱,齐顷公、逄丑父是也。夫冒大辱以生,其情无乐,故贤人不为也,而众人疑焉,春秋以为人之不知义而疑也,故示之以义,曰:'国灭,君死之,正也。'正也者,正于天之为人性命也,天之为人性命,使行仁义而羞可耻,非若鸟兽然,苟为生,苟为利而已。是故春秋推天施而顺人理,以至尊为不可以加于至辱大羞,故获者绝之;以至辱为亦不可以加于至尊大位,故虽失位,弗君也;已反国,复在位矣,而春秋犹有不君之辞,况其溷然方获而虏邪!其于义也,非君定矣,若非君,则丑父何权矣!故欺三军,为大罪于晋,其免顷公,为辱宗庙于齐,是以虽难,而春秋不爱。丑父大义,宜言于顷公曰:'君慢侮而怒诸侯,是失礼大矣;今被大辱而弗能死,是无耻也;而复重罪,请俱死,无辱宗庙,无羞社稷。'如此,虽陷其身,尚有廉名,当此之时,死贤于生,故君子生以辱,不如死以荣,正是之谓也。由法论之,则丑父欺而不中权,忠而不中义,以为不然,复察春秋,春秋之序辞也,置王于春正之间,非曰:上奉天施,而下正人,然后可以为王也云尔!今善善恶恶,好荣憎辱,非人能自生,此天施之在人者也,君子以天施之在人者听之,则丑父弗忠也,天施之在人者,使人有廉耻,有廉耻者,不生于大辱,大辱莫甚于去南面之位。而束获为虏也。曾子曰:'辱若可避,避之而已;及其不可避,君子视死如归。'谓如顷公者也。"
"春秋曰:'郑伐许。'奚恶于郑,而夷狄之也?"曰:"卫侯卒,遫郑师侵之,是伐丧也;郑与诸侯盟于蜀,以盟而归诸侯,于是伐许,是叛盟也。伐丧无义,叛盟无信,无信无义,故大恶之。"问者曰:"是君死,其子未逾年,有称伯不子,法辞其罪何?"曰:"先王之制,有大丧者,三年不呼其门,顺其志之不在事也。书曰:'高宗谅闇,三年不言。'居丧之义也。今纵不能如是,奈何其父卒未逾年,即以丧举兵也。春秋以薄恩,且施失其子心,故不复得称子,谓之郑伯,以辱之也。且其先君襄公,伐丧叛盟,得罪诸侯,诸侯怒之未解,恶之未已,继其业者,宜务善以覆之,今又重之,无故居丧以伐人;父伐人丧,子以丧伐人;父加不义于人,子施失恩于亲,以犯中国;是父负故恶于前,己起大恶于后,诸侯毕怒而憎之,率而俱至,谋共击之,郑乃恐惧去楚,而成虫牢之盟是也。楚与中国,侠而击之,郑罢弊危亡,终身愁辜。吾本其端,无义而败,由轻心然。孔子曰:'道千乘之国,敬事而信。'知其为得失之大也,故敬而慎之。今郑伯既无子恩,又不庸计,一举兵不当,被患不穷,自取之也。是以生不得称子,去其义也;死不得书葬,见其穷也。曰:有国者视此,行身不放义,兴事不审时,其何如此尔。"
《春秋繁露》 汉·董仲舒
《春秋》之常辞也,不予夷狄,而予中国为礼,至邲之战,偏然反之,何也?"曰:"《春秋》无通辞,从变而移,今晋变而为夷狄,楚变而为君子,故移其辞以从其事。夫庄王之舍郑,有可贵之美,晋人不知其善,而欲击之,所救已解,如挑与之战,此无善善之心,而轻救民之意也,是以贱之,而不使得与贤者为礼。秦穆侮蹇叔而大败,郑文轻众而丧师,《春秋》之敬贤重民如是。是故战攻侵伐,虽数百起,必一二书,伤其害所重也。"问者曰:"其书战伐甚谨,其恶战伐无辞,何也?"曰:"会同之事,大者主小,战伐之事,后者主先,苟不恶,何为使起之者居下,是其恶战伐之辞已!且《春秋》之法,凶年不修旧,意在无苦民尔;苦民尚恶之,况伤民乎!伤民尚痛之,况杀民乎!故曰:凶年修旧则讥,造邑则讳,是害民之小者,恶之小也;害民之大者,恶之大也,今战伐之于民,其为害几何!考意而观指,则《春秋》之所恶者,不任德而任力,驱民而残贼之;其所好者,设而勿用,仁义以服之也。《诗》云:'弛其文德,洽此四国。'此《春秋》之所善也。夫德不足以亲近,而文不足以来远,而断断以战伐为之者,此固《春秋》所甚疾已,皆非义也。"难者曰:"春秋之书战伐也,有恶有善也,恶轴击而善偏战,耻伐丧而荣复雠,奈何以《春秋》为无义战而尽恶之也?"曰:"凡春秋之记灾异也,虽亩有数茎,犹谓之无麦苗也;今天下之大,三百年之久,战攻侵伐,不可胜数,而复雠者有二焉,是何以异于无麦苗之有数茎哉!不足以难之,故谓之无义战也。以无义战为不可,则无麦苗亦不可也;以无麦苗为可,则无义战亦可矣。若《春秋》之于偏战也,善其偏,不善其战,有以效其然也。春秋爱人,而战者杀人,君子奚说善杀其所爱哉!故《春秋》之于偏战也,犹其于诸夏也,引之鲁,则谓之外,引之夷狄,则谓之内;比之轴战,则谓之义,比之不战,则谓之不义;故盟不如不盟,然而有所谓善盟;战不如不战,然而有所谓善战;不义之中有义,义之中有不义;辞不能及,皆在于指,非精心达思者,其庸能知之!诗云:'棠棣之华,偏其反而;岂不尔思,室是远而。'孔子曰:'未之思也!夫何远之有?'由是观之,见其指者,不任其辞,不任其辞,然后可与适道矣。"
"司马子反为君使,废君命,与敌情,从其所请,与宋平,是内专政,而外擅名也。专政则轻君,擅名则不臣,而春秋大之,奚由哉?"曰:"为其有惨怛之恩,不忍饿一国之民,使之相食。推恩者远之为大,为仁者自然为美。今子反出己之心,矜宋之民,无计其闲,故大之也。"难者曰:"《春秋》之法,卿不忧诸侯,政不在大夫。子反为楚臣,而恤宋民,是忧诸侯也;不复其君,而与敌平,是政在大夫也。湨梁之盟,信在大夫,而春秋刺之,为其夺君尊也;平在大夫,亦夺君尊,而《春秋》大之,此所闲也。且《春秋》之义,臣有恶擅名美。故忠臣不显谏,欲其由君出也。《书》曰:'尔有嘉谋嘉猷,入告尔君于内,尔乃顺之于外,曰:此谋此猷,惟我君之德。'此为人臣之法也;古之良大夫,其事君皆若是。今子反去君近而不复,庄王可见而不告,皆以其解二国之难,为不得已也,奈其夺君名美何!此所惑也。"曰:"《春秋》之道,固有常有变,变用于变,常用于常,各止其科,非相妨也。今诸子所称,皆天下之常,雷同之义也;子反之行,一曲之变,独修之意也。夫目惊而体失其容,心惊而事有所忘,人之情也;通于惊之情者,取其一美,不尽其失。诗云:'采葑采菲,无以下体。'此之谓也。今子反往视宋,闻人相食,大惊而哀之,不意之至于此也,是以心骇目动,而违常礼。礼者,庶于仁,文质而成体者也。今使人相食,大失其仁,安着其礼,方救其质,奚恤其文,故曰:'当仁不让。'此之谓也。《春秋》之辞,有所谓贱者,有贱乎贱者,夫有贱乎贱者,则亦有贵乎贵者矣。今让者,《春秋》之所贵,虽然,见人相食,惊人相爨,救之忘其让,君子之道,有贵于让者也,故说春秋者,无以平定之常义,疑变故之大,则义几可谕矣。"
《春秋》记天下之得失,而见所以然之故,甚幽而明,无传而着,不可不察也。夫泰山之为大,弗察弗见,而况微眇者乎!故按春秋而适往事,穷其端而视其故,得志之君子、有喜之人,不可不慎也。齐顷公亲齐桓公之孙,国固广大,而地势便利矣,又得霸主之余尊,而志加于诸侯,以此之故,难使会同,而易使骄奢,即位九年,末尝肯一与会同之事,有怒鲁卫之志,而不从诸侯于清丘断道,春往伐鲁,入其北郊,顾返伐卫,败之新筑;当是时也,方乘胜而志广,大国往聘,慢而弗敬其使者,晋鲁俱怒,内悉其众,外得党与卫曹,四国相辅,大困之鞍,获齐顷公,斮逄丑父。深本顷公之所以大辱身,几亡国,为天下笑,其端乃从慑鲁胜卫起;伐鲁,鲁不敢出;击卫,大败之;因得气而无敌国,以兴患也。故曰:得志有喜,不可不戒。此其效也。自是之后,顷公恐惧,不听声乐,不饮酒食肉,内爱百姓,问疾吊丧,外敬诸侯,从会与盟,卒终其身,家国安宁。是福之本生于忧,而祸起于喜也。呜呼!物之所由然,其于人切近,可不省邪!
"逄丑父杀其身以生其君,何以不得谓知权?丑父欺晋,祭仲许宋,俱枉正以存其君,然而丑父之所为,难于祭仲,祭仲见贤,而丑父犹见非,何也?"曰:"是非难别者在此,此其嫌疑相似,而不同理者,不可不察。夫去位而避兄弟者,君子之所甚贵;获虏逃遁者,君子之所甚贱。祭仲措其君于人所甚贵,以生其君,故春秋以为知权而贤之;丑父措其君于人所甚贱,以生其君,春秋以为不知权而简之。其俱枉正以存君,相似也,其使君荣之,与使君辱,不同理。故凡人之有为也,前枉而后义者,谓之中权,虽不能成,春秋善之,鲁隐公、郑祭仲是也;前正而后有枉者,谓之邪道,虽能成之,春秋不爱,齐顷公、逄丑父是也。夫冒大辱以生,其情无乐,故贤人不为也,而众人疑焉,春秋以为人之不知义而疑也,故示之以义,曰:'国灭,君死之,正也。'正也者,正于天之为人性命也,天之为人性命,使行仁义而羞可耻,非若鸟兽然,苟为生,苟为利而已。是故春秋推天施而顺人理,以至尊为不可以加于至辱大羞,故获者绝之;以至辱为亦不可以加于至尊大位,故虽失位,弗君也;已反国,复在位矣,而春秋犹有不君之辞,况其溷然方获而虏邪!其于义也,非君定矣,若非君,则丑父何权矣!故欺三军,为大罪于晋,其免顷公,为辱宗庙于齐,是以虽难,而春秋不爱。丑父大义,宜言于顷公曰:'君慢侮而怒诸侯,是失礼大矣;今被大辱而弗能死,是无耻也;而复重罪,请俱死,无辱宗庙,无羞社稷。'如此,虽陷其身,尚有廉名,当此之时,死贤于生,故君子生以辱,不如死以荣,正是之谓也。由法论之,则丑父欺而不中权,忠而不中义,以为不然,复察春秋,春秋之序辞也,置王于春正之间,非曰:上奉天施,而下正人,然后可以为王也云尔!今善善恶恶,好荣憎辱,非人能自生,此天施之在人者也,君子以天施之在人者听之,则丑父弗忠也,天施之在人者,使人有廉耻,有廉耻者,不生于大辱,大辱莫甚于去南面之位。而束获为虏也。曾子曰:'辱若可避,避之而已;及其不可避,君子视死如归。'谓如顷公者也。"
"春秋曰:'郑伐许。'奚恶于郑,而夷狄之也?"曰:"卫侯卒,遫郑师侵之,是伐丧也;郑与诸侯盟于蜀,以盟而归诸侯,于是伐许,是叛盟也。伐丧无义,叛盟无信,无信无义,故大恶之。"问者曰:"是君死,其子未逾年,有称伯不子,法辞其罪何?"曰:"先王之制,有大丧者,三年不呼其门,顺其志之不在事也。书曰:'高宗谅闇,三年不言。'居丧之义也。今纵不能如是,奈何其父卒未逾年,即以丧举兵也。春秋以薄恩,且施失其子心,故不复得称子,谓之郑伯,以辱之也。且其先君襄公,伐丧叛盟,得罪诸侯,诸侯怒之未解,恶之未已,继其业者,宜务善以覆之,今又重之,无故居丧以伐人;父伐人丧,子以丧伐人;父加不义于人,子施失恩于亲,以犯中国;是父负故恶于前,己起大恶于后,诸侯毕怒而憎之,率而俱至,谋共击之,郑乃恐惧去楚,而成虫牢之盟是也。楚与中国,侠而击之,郑罢弊危亡,终身愁辜。吾本其端,无义而败,由轻心然。孔子曰:'道千乘之国,敬事而信。'知其为得失之大也,故敬而慎之。今郑伯既无子恩,又不庸计,一举兵不当,被患不穷,自取之也。是以生不得称子,去其义也;死不得书葬,见其穷也。曰:有国者视此,行身不放义,兴事不审时,其何如此尔。"
《春秋繁露》 汉·董仲舒